

来源:湖南作家网 时间 : 2025-11-22
分享到:
小说《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
以自然映照人心
文 | 李兰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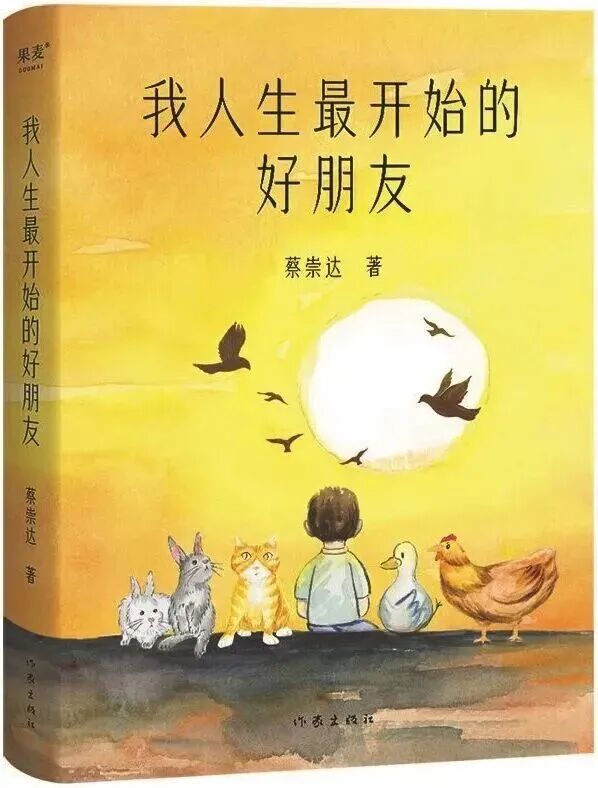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蔡崇达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2月
去年此时,《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即将成书,这是我图书编辑生涯中责编的第一部作品。往返于这条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我喜欢上班走亮马河北岸,下班走南岸。背包里的校样有点儿沉,打印在A4纸上的故事中,千里之外的闽南小镇,男孩黑狗达刚刚失去他的外婆。外婆的母亲——阿太来了,她的箩筐里装满小鸭子,渐渐地,黑狗达认出了那只代替外婆来爱他的鸭子小白。
鸭子小白、老母鸡阿花、花猫黑咪、兔子佐罗,还有鸽子米点和雪花,阿太用扁担挑来的动物朋友们,陪伴黑狗达的童年、少年时期,陪伴他的一家人。阿太教会她的孩子们如何与动物交朋友,如何与万物交朋友。这位命运多舛的乡间老人,她已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孙辈,却总是能够出现在最需要爱的那一个面前。她是乡野的智者,深谙这片土地、这个民族古老的秘密与哲学。人生而孤独,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天地之间,只有和万物交朋友,才能与孤独、离别和解,才能与生死和解。
“崇尚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基础,作为文化基因沉淀在中国人的血脉里,延续千年。20世纪80年代的福建东石镇,那位耄耋老人的血脉中与万物共生的基因始终在流淌。黑狗达的阿太,她的日夜漫长,长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生离死别。她以植物为伴,挑着各种小动物的扁担的另一头,永远是她的那些花花草草。阿太坐在花草中间,和它们说话,掐几枝盛开的海棠和茉莉插到自己盘好的发髻上,黑狗达终于明白故乡的老人家头上的簪花是从哪儿来的,原来他们都擅长和植物为伴。阿太和黑狗达眼中的小动物,皆是人一样的存在,鸭子小白回到了大海,老母鸡阿花是一个扬善除恶的侠客,兔子佐罗执着于为爱人复仇,花猫黑咪守护着父亲的加油站以及乡邻的一方平安,鸽子米点和雪花随着父亲的离去而离去,随着黑狗达的归来而归来,邻居家的土狗大黄认得离乡经年的黑狗达,并且懂得他的悲伤……世间万物,和阿太是平等的,和黑狗达是平等的。
黑狗达在与一个个小动物的短暂相聚和必然告别中,体会着生命的流逝与意义。孤独是常态,离别是常态,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治愈,让这一家人被万物拥抱,生死不能摧毁他们,他们葆有了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阿太像是大地之母,她承载苦痛、接纳新生,她视消逝为“归去”,人从自然中来,等离开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回到自然中去。“天地悠悠,苍老而可靠。”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尊重儿童主体性,以孩子的视角呈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朴素认知。在古老而新生的自然话语中,这本书还关注闽南的乡村伦理和秩序,随着东石这座海边小镇的发展,平静的宗族社会出现了很多新鲜事物,比如盗贼。偷大白猪的盗贼被勇猛孤傲的老母鸡阿花击退,而小镇的人们对盗贼的认识——外来人一多,暂时还没找到可以安身的工作,吃不了饭,就只能偷了,以及“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日常行为规约,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秩序的宽仁和温厚,让我们思考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当代精神价值。
我始终认为,好的儿童文学不仅仅是孩子的读物,它能够体现人类共通情感,探讨人类共同价值。告别和交朋友是生命与成长的必修课。《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讲述的是闽南小镇上一个普通家庭的温暖故事,这是关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故事,也是关乎传统与时代、家与国的故事。
今天再次翻开这本书,坐在亮马河边,一年的时光从眼前倏忽而过。我想象孩子们阅读的感受,不远处,东北三环上车声鼎沸,但这里似乎永远静谧,也许河水吸纳了所有,连喧嚷都是静谧的……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责任编辑)
小说《万花筒》
“万花筒”旋出的缤纷世界
文 | 阮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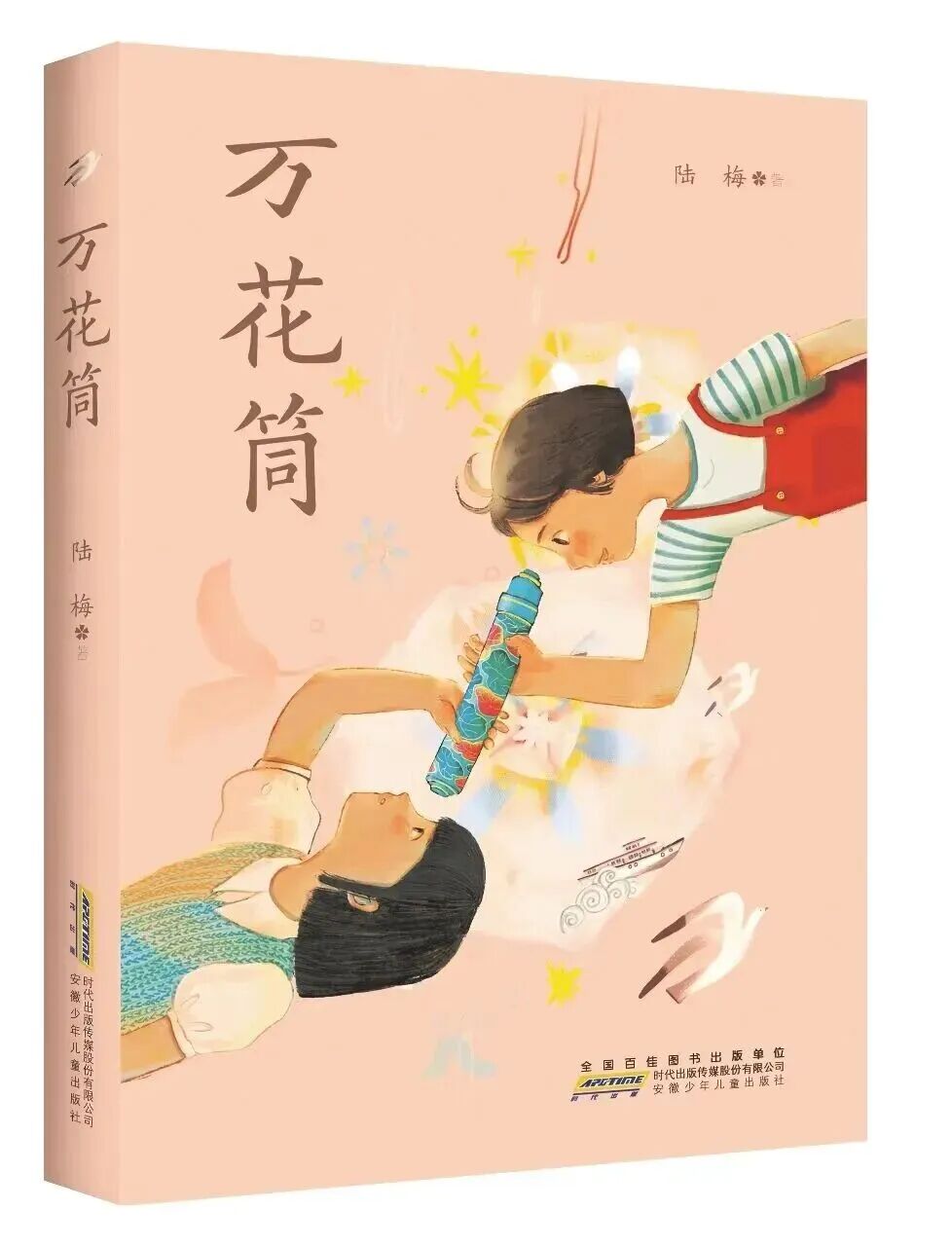
《万花筒》,陆梅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5月
陆梅老师自2020年初夏开始创作《万花筒》,2021年底改定。其间,她谈起这一创作计划和进度,我内心很是雀跃。2021年下半年,我们编辑团队跟随欧阳春总编辑去上海拜访陆梅老师,我们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41楼的《文学报》编辑部畅谈,双方就《万花筒》这部书稿的合作达成了默契与共识。透过41楼的落地窗,俯瞰外滩现代化与历史特色完美融合的城市景观,我知道自己即将有幸经由陆梅老师的笔端,获得在这座城市驻足并凝望的机会。
《万花筒》初稿的完成度之高,超乎我的想象,尤其是充满匠心的细节雕琢,印证了陆梅老师一贯细腻、严谨的创作态度与习惯。我一口气读完,内心不停地涌动着,记录下约3000字的最初的阅读感受,发给陆梅老师讨论。我当时这样写道:“在《万花筒》这部小说中,我们跟随主角,从梅家坞到芦荻镇,再到大上海的永年里,那些熟悉的地名、路名、建筑、小吃……充满人间烟火的海派文化生活,以及那些富有年代感的人物角色,和他们各自独特的出身、性格、命运,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蓬勃向上的城市氛围。‘万花筒’旋出的缤纷世界,这是少女精神故乡里的梦幻的夏天世界,也是兼容并包、开放创新的上海的世界,更是富有生活质感和人性关怀的中国的世界……如果从宏大的格局,回到少女小说的范畴里看,这部作品有着和您之前作品《格子的时光书》《无尽夏》中对少女心理嬗变同样深刻细腻的刻画,又更多地承载了反映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意义与功能;关于时空交替转换的叙述,我个人认为比《格子的时光书》处理得更加娴熟,又与《格子的时光书》产生了呼应与联结。其中,麦小节迷路的情节尤其令我痴迷,这就是活灵活现的童年现场——每个孩子,都会经历一次迷路,一次生病,一次紧张兮兮,一次大汗淋漓……经历后就是成长。长大后每次回想那个场景,都会恋恋不舍、恍若隔世。这绝对是少女小说写不尽的经典情节。”
基于对作品这样的认识基础,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了。陆梅老师的写作非常讲究文字的韵律与节奏,她又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因此《万花筒》的语言特色非常鲜明。评论家李东华称她的叙述“讲究、节制、清雅,时时有禅意,充分释放了汉语言的魅力”;评论家刘琼称其具有“学院派写作的细致文雅”;评论家徐妍总结为“轻声细语的沪声沪语”。因此,在编辑《万花筒》的过程中,关于如何在最大限度体现陆梅老师的文学语言张力、凸显沪语特色的同时,兼顾各地小读者对方言的理解能力,我与陆梅老师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我们决定尽量完整保留石库门群众的沪语对话,力求做到原汁原味,并在文下以注释的形式对方言进行解释。于是,我们这些来自安徽的编辑跟着《万花筒》,学起了上海话——当麦小节的奶奶谈起白雪的爸爸白海翔时说:“伊拉爸爸海员嘛,钞票赚得动。等一歇睏个中觉,勿要再上去了。”我们学会了“伊拉”是沪语里的人称代词,此处指女孩白雪,“睏”则是沪语“睡觉”的意思……类似这样生动的沪语表达还有很多,这令我们在编辑书稿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上海石库门那一条条小小的弄堂里,耳边洋溢着软糯婉转的沪声沪语,眼前是更加生动的一片人间烟火。
陆梅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关于《万花筒》的图书呈现形式,她给予我们很多独到的建议。她希望这本书拿在手上感觉轻巧、方便,书页订口处易翻,给读者天然的亲近感。于是,我们放弃使用大克重的纸张,选择本白色的轻型纸印刷。内文插图以手绘场景图为主,用带有做旧感的低饱和配色增强石库门的历史感;篇章页以放大的“永年里”插画作为背景,篇章标题正好放在弯弯的拱门下,营造故事的纵深感;封面则以淡粉色打底,两位少女主角顶着童花头的稚气形象,一上一下,共同托举着一架万花筒,从头尾的孔洞里探望对方,形成了对角线的美感效果,恰到好处地呼应着作品中两位少女互为镜像的人物关系,书名用正楷字体印刷,清新、质朴。
《万花筒》出版后,为了拍摄作品背景视频,收集宣传推广素材,我和编辑高静与陆梅老师相约同游上海石库门。我们逛张园、新天地,从合肥路走到顺昌路,拍摄拆迁中的老建筑。陆梅老师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就像麦小节那样,从郊区松江辗转换车,来到上海市区的石库门弄堂,住进奶奶家。去年,她去那里散步,还偶遇了一个临时展览,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重现顺昌路的百年烟云……完成了石库门的拍摄,我们直奔北外滩,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区域架起摄像机,拍摄黄浦江上过往的船只,感受书中白海翔坐在远洋轮上驶出港口的那份壮志豪情。当时,书中最打动我的情节又浮现脑海:为了鼓励女儿白雪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挫折,白海翔这位父亲航行在大海上给女儿写信,讲述中国远洋货轮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以及个人和时代、国家的命运牵绊,当他乘坐挂着国旗的中国船驶向世界,就会由衷地感到自豪——“只要出海远航,一艘船就是一片浮动的国土。”这饱含泪点的真切的文字,如今仍令我动容,每每重读都点燃我作为童书编辑的使命感。这是属于时代的真诚的儿童文学,理应讲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儿童。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席编辑、《万花筒》策划编辑之一)
诗歌《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
作家和编辑互为灯塔
文 | 孙玉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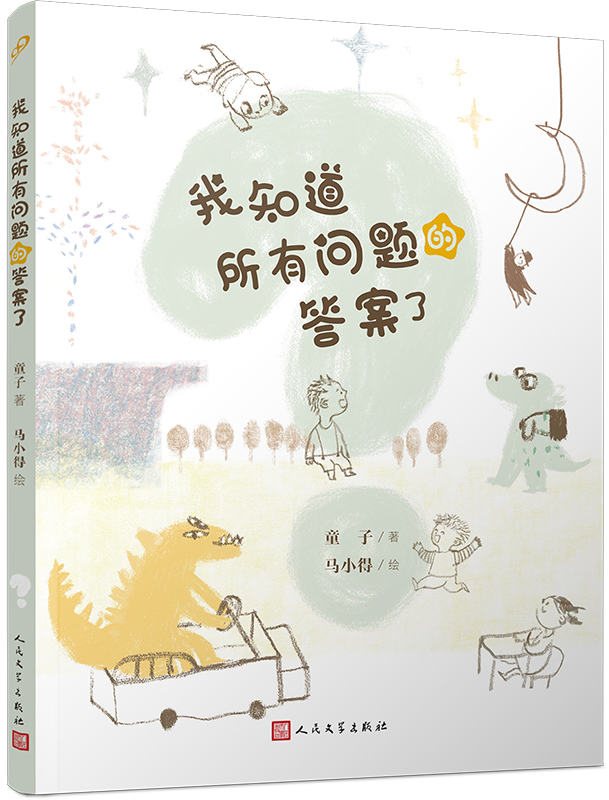
《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童子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5月
写这篇编辑手记之前,我花了78块钱从网上淘来一本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2006年第10期《少年文艺》(当年这本杂志的售价是3元5角),上面有一首童子的组诗《兔子日记》——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和童子的诗最初的相遇。我想进一步确认,童子早期诗歌的模样。
2006年,我19岁,是一名大二学生。19年后重读,我发现,童子的诗在最开始出发的时候就是新鲜灵动的。他以兔子的口吻写下:“我遇到一个迷了季节的格子衫男孩/他以为这里是夏天呢/我告诉他,夏天要往上边走才对”。他还写道:“我有了一头小毛驴/昨晚我把它拴在门口美丽的野豌豆上/清早它和野豌豆一起失踪了”。19年后,我在童子的诗集《赤足跳来跳去》里遇到了另一个句子:“我有一匹勇敢的小马/为了让它安静、听话/每天我都把它拴在小雏菊的梗儿上”。小毛驴是可以拴在野豌豆上的,小马是可以拴在小雏菊的梗儿上的。在童子的童诗宇宙里,这种通过空间反差构建出来的诗意,跨越19年的时光,如此统一。
我和童子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12年左右,他在国贸上班,我在永安里上班,我下班后坐一站地铁就去找他了。此后,我们在线下见过很多次,我也读了他的很多童诗和童话,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童子的诗集,直到我在2021年第12期《十月少年文学》的头条读到了组诗《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心底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它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童子集中笔力去写同一个主题,而且是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思考,这份探索的勇气和创作的野心很难不让人心动。
我对童子说,我想出版《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但是诗的数量有点少,能不能围绕这个主题再写一些。童子很快答应下来。2022年1月11日,童子发来40首左右的诗稿,同时他还告诉我已经完成一部动物主题的诗集,但还没有编排。2022年1月20日,童子发来那部动物主题诗集《新新动物学堂》(后更名为《赤足跳来跳去》)。最终当我告诉他,两本诗集可以一起出版,我能明显感觉到微信对话框另一边的童子内心的喜悦。那时候出诗集已经很难了,何况还是两本。
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因为这两本童诗集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气质,一本思考生命,一本传递快乐。在童书市场的逻辑下,两本打包销售,亮点多了一个,打“骨折”后价格也划算,蛮好。
我请有着丰富诗集编辑经验的郭良忠跟我一起来做这两本书,并在童子的推荐下,约了插画师马小得来创作插图。书,很顺利地就做出来了。两本书组了个套装,谓之“献给孩子和大人的童诗大餐”。
然而,在报送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时候,我们却犯了难。因为,两本都很好。《赤足跳来跳去》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很“童诗”的童诗,童趣盎然,很轻盈;《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也是有童趣的,但它在轻盈中注入了思考的力量,是一种负重的飞翔。从童诗的接受度来说,选择后者是一种冒险,因为它打破了童诗的某些既定范式,在不断地探索童诗的边界和可能性。对习惯于读很“童诗”的童诗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冒犯”。
经过短暂的纠结之后,最终我们还是坚定地报了《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这个决定虽然有点冒险,但有着鲜明的态度:我们认为童诗不应该总是千人一面,除了童趣,它还可以容纳更广阔的内容。
后来,就是获奖的消息传来。
因为筹备颁奖典礼,导演组发来沟通提纲。在答复的过程中,我征求童子的意见:可以提你耳朵的事情吗?童子回复我: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没必要特意提,一旦提了就被贴上标签。我说,好的,那我不提。
但叙述就是这么有圈套,那里不提,为了写这篇编辑手记,我还是会写到这个细节。就是那年我和童子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有一只耳朵戴了助听器。我心头一震,好想抱抱他。尔后的很多年里,我几乎忘了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看来童子说得对,我们只需要读他的诗就好。
行文至此,我很想全文引用《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里的这首《星星和星星互为灯塔》:
星星和星星互为灯塔,/它们朝着对方在走。//什么时候才会相遇呢?/几万年过去了。//而我和你呀,你和我呀,/也正朝着对方在走。//亿万年前的两颗星星,/就要相遇了。//地球就是星星聚会的地方呀,/转瞬,又一万年过去了。//而你和我呀,我和你呀,/已经紧紧握住了手。
那天看到评论家涂明求在朋友圈说,作家和评论家互为灯塔。我想说,作家和编辑也是互为灯塔的关系,我们只要一直向前走,总会遇到心灵契合的合作者,总会找到一颗值得我们为之停留的星星。
下一次,如果再让我遇到这样的时刻,我一定还会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心底默念:就是你了。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副总编辑、《我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责任编辑之一)
童话《白夜梦想家》
在白夜中寻光
文 | 吴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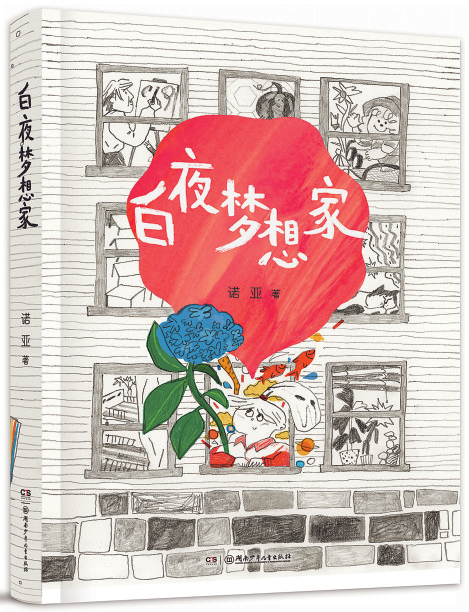
《白夜梦想家》,诺亚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0月
与诺亚相识于十多年前,我们曾同期入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同住一栋宿舍楼。不久后她便离职投身创作,但我始终关注着她的成长轨迹——从初涉儿童文学,到出版首部作品,再到佳作频出,在儿童文学领域渐放光彩。
诺亚始终将目光聚焦于那些独特的孩子:《哑江》里于平凡中创造美的“田傻子”;《云上日光》里凭借通感描绘内心色彩的乔安安……这些鲜活的人物让我对《白夜梦想家》中的“梦想家”充满期待——它必将承载诺亚对儿童心灵最深刻的理解与最温柔的守护。
以童真走进童心:写故事的人,心里住着孩子。丰子恺先生曾说:“做人得有点‘童心’。”这句话在诺亚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她总谦称自己不算真正的作家,只是一个喜欢孩子的写作者。但在我眼中,她更是一位儿童心灵的守护者——不仅自己葆有纯净的童心,更能以独特的方式走进孩子的世界,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守护他们珍贵的童真。
读者常称赞她想象力天马行空,诺亚却说:“在真正的孩子面前,成人的想象总是显得匮乏。想象力源于一颗永远好奇的心。”因此,在每一次面对孩子的讲座中,她总是不厌其烦地鼓励他们:“要像种子对泥土外的天空保持好奇那样,对生活充满期待。”这份好奇是真诚的。她因为好奇猫,所以研究猫;因为好奇种子,所以观察种子;因为好奇云,所以天天抬头看云。这种永不熄灭的好奇,正是她创作灵感的源泉。
以精心雕琢文本:九易其稿,唯愿不负初心。一本好书的重中之重,首先在于文稿质量。诺亚对此极为认真。她交稿时告诉我,稿件已修改七次,正在进行第八次打磨。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持续沟通,反复推敲。令我惊叹的是,每当我觉得某处已足够精彩,她总能发现可精进的细节。最终交到我手中的稿子,已是第九版——与初稿相比已是脱胎换骨,部分章节甚至只字不留,全部重写。对此诺亚坦言:“这是一个大工程,重写未必结果更好,但这是我献给父亲和童年自己的书,不愿留下太多遗憾。”她补充道:“写作有时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若我缺乏这份勇气,读我作品的孩子,或许也难以在面对苦难时勇敢前行。”
改稿过程中,一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故事中“北极星”所使用的彩虹棒,原本只是一根普通木棍。经汤素兰老师点拨,改为由彩虹幻化而成,堪称神来之笔。“北极星”作为父亲的化身,是守护者,也是引路人,陪伴主角在奇遇中认识自我、学会自爱。而那根彩虹棒,则成为“父爱”的象征,预示着梦想家突破自我后,即将绽放的绚烂未来。
以梦想构筑世界:用插画为文字插上翅膀。优秀的图文设计是内容的延伸,能提升阅读的共鸣与记忆。诺亚对插画的高要求让我倍感压力,苦寻插画师未果之际,总编辑胡隽宓推荐了周琛老师。周琛老师读完试读本后,迅速提交了一份涵盖人物解读、色彩方向和插画构思的完整方案,其专业与认真令人动容,诺亚与总编辑都赞誉有加。我们一致决定给予她最大的创作自由。经反复推敲,我们确定以灰色象征现实的困惑,红色代表梦想的热情。当文字与视觉如此相融,图书便真正拥有了生命。
文字、图像、设计的精妙配合决定了一本书的“用户体验”。当这些元素形成有机整体时,一本书便真正拥有了生命力,《白夜梦想家》就是这样一本有生命力的书。
以温度传递力量:我们都在守护童年的光。真正有温度的儿童文学,是能够温暖和治愈孩子心灵的。我始终认为,守护童心成长,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出版人、评论家与推广人共同的责任。
《白夜梦想家》出版后,我们举办了作品研讨会。总编辑胡隽宓在会上的一席话,精准道出了我们的出版初衷:“今天的孩子,虽未必经历物质匮乏,却常陷于信息时代的深层孤独。他们的想象空间被现实挤压,内心敏感而脆弱,更容易在价值多元的世界里感到不安与迷茫,产生生命的‘失重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白夜梦想家》这样的作品,来抚慰孤独、拓展想象,引导他们建立自我认同,看见更广阔的生命选择。”
这份初衷,在读者那里得到了温暖回应。我至今记得,研讨会上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燕玲特意请诺亚签名,希望与她经历相似的侄女能从书中获得成长的力量。在北京的分享会上,一位父亲动情地说:“这是一本需要反复阅读的书,伏笔精巧,亲情的描写常让我热泪盈眶。”这些瞬间让我深深感动:原来有这么多大朋友,正与我们一同默默守护着孩子们的童心。
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编辑,我深信童心是成长中最宝贵的财富。编辑《白夜梦想家》于我而言,不仅是一次工作,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愿未来能继续编撰更多好书,也期待更多人携手同行,共同守护童心,为孩子们构筑一个更温暖、更斑斓的文学世界。
(作者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高级策划编辑、副编审,《白夜梦想家》责任编辑之一)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