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时间 : 2013-12-16
分享到:

关于成长小说
施战军
成长小说这个题目我以前就讲过一次,一般讲过了都不想再讲了。但这次有了很大的更新,这个更新的机缘就在于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块儿说话,有个朋友说到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现在已经24岁了,他女儿在中学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他知道后告诉他女儿说,你不要这样,他女儿和他们承诺说不会再来往了。等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家人着急说你应该交男朋友了,女儿就把她男朋友领回家了,一看发现还是以前那个。他很不理解,就问他女儿说,你是北京一所名校的大学生,而你的男朋友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的大学生。他女儿说,和你们这代人相比,我们这代人相处不仅仅是情投意合。这句话让他激动了,他好久好久还在想这句话:现在这代人,尤其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这批孩子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和选择?其实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几乎大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成长过程的孤独感,导致一切感情都浓缩成男女交往恋爱结婚,它是一个复合体。不像我们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讲到爱情那就是纯爱,成长所需要的条件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当初我们看到的很多成长小说,他的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对今天这代人的成长已经不理解,已经很难用自己的经历去理解这代人,(因为)这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复杂性。而成长对于我们这批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成长具有时代性和时段性。比如像王蒙这一代作家,他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可以放到成长小说里来,它都是一种“回望型”的写作,带有一种争议性质,这种争议性使得我们在回顾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往往脱离了第一人称的叙述。第一人称是以我出现,但在叙事的层面上依然是一个第三人称“他”这个和国外的成长小说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知道成长小说的概念是完全从国外来的,我们首先从人称上看,无论是歌德的成长小说,还是马克·吐温的成长小说,还是到了美国上个世纪颓废一代他们的成长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面目出现,是一种“我”成长。中国人的成长小说往往是一种被成长,所以它一般是第三人称的态度。
再看西方的成长小说里的主人公,他是“野的”,而不是家养的。在野的成长中,我们的主人公一般都是野小子的性格。他在小说里基本活动的环境都是户外,而我们中国的成长小说都是被看着长大的。如果说西方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是野孩子系列,那么我们中国的成长小说就是坏孩子系列和好孩子系列。伦理标准是第一标准,如果说西方的成长小说成长的环境是在户外,中国的就是在家住。学校也是家,社会也是家,家庭更是家。在西方的成长里面我们看到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就像成人一样,像殖民者一样,有了冒险的冲动和勇气。西方成型的成长小说都叫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这是马克·吐温最重要的两部小说。马克·吐温他作为美国现代美国文学之父,就是因为这样小说的存在。甚至像海明威这样牛的一位作家,他曾经评价马克·吐温说,一切现代美国文学都来自一本书叫《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它说的是真实冒险,摆脱喧嚣的生活环境,达到一种自由的生活境界。所有的美国精神、关于美国精神的叙述、关于民主自由,一切主题都能从马克·吐温这里找到。所有后来写作的几乎都是从马克·吐温这颗大树上生出来的小树叶,然后继续长,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他笔下的硬汉的形象就是就是长大了的自己。美国其他的作家像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们把他和哈克对比,远远不如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后来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垮掉的一代,他们开始反思过去的所谓的美国精神的写作,用一种怀疑的、颓废的、逆反的心智来写小说,就出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他的背板其实依然是马克·吐温。不过马克·吐温他是在正面踢球,他是把球弹到马克·吐温身上再反弹回来。历险记似的描写,像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等,都是属于这一脉。成长、冒险、占有,通过占有来体现某种精神的强大等。它里面有基督教的背景。包括犯罪,忏悔。而我们呢?我们的成长小说模式是这样的——我们也有成长,但是我们长不大,长不完。长不大的这种成长,导致我们心智开始发达的时候有一种叛逆的冲动,而不是冒险的冲动。冒险是主动的,而我们是叛逆的,可是叛逆来叛逆去,人长到二十来岁又回到了童年被管教的时代,一个归驯的时期。而且还不止是自己归驯,还继续向下一代归训那一套伦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成长,中国人没长完,在成家以后还有叛逆期,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什么七年之痒啊等等这些说法。他有个叛逆期,他有破坏的冲动,寻求刺激的冲动。因为少年时这种刺激不够充分,所以现在中国的家庭出现了很多不稳固的状态,结婚几年就出现了什么单亲家庭,又重新进入了叛逆的循环。到老了以后,你会发现许多这些作家们都有一个问题,老了之后开始算账,这一辈子如何如何。中国作家特别愿意写回忆录,他开始算账,算什么呢?主要是算自己恨的那些人,看和一辈子遇上多少风浪,多少人和自己过不去,他会非常充分的在作品里写出来。我们现在看很多老作家,他们后来强调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如果西方的文学作品归于为人类精神的忏悔,我们中国的作家通过他这样一个人生的过程,从算账归到一种怨恨。人生充满了埋怨,所以精神上还是没长大。他一辈子就算活到一百岁也白费,包括巴金他也是这样。只有一个人少年老成,长完了,但是他英年早逝——鲁迅就是这个人,但他英年早逝。第三人称的成长和第一人称的成长确实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概念。
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我们怎样做父亲》,他对比了欧洲人的成长,和我们中国的成长,鲁迅说往昔的欧洲人对孩子的误解,是作为成人的预备。孩子是干什么的呢?成人的预备。中国人怎么说的?说中国人的误解是自以为缩小的成人。无论我们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还是亲朋好友的孩子,还是在电视里看到的少儿节目,尤其是少儿的节目,你看见那些孩子说的话都是小大人似的。而且我们很多人认为小大人是可爱的,父母总是从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的儿女学习好一定要让很多人知道,他会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是缩小的成人,完全是自己影子的投射。而西方呢,他是成人预备,他要长成成人的,他要负责的。这是一个不同的理解。

其实误解都是有的,鲁迅看到了这一点,孩子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是无法确切看到的。在误解里,中西方有对峙。就是在对峙的刹那产生了成长小说,因为孩子自己写成长小说是不可能的,要成人来写,在自己的笔下给孩子什么样的自由?让他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这是关键。这种小说无一例外的都有一种家长的眼光,但是每个家长的眼光是不同的。中国家长的眼光是让孩子长成他所期盼的样子,所以我们的大人就会冒充孩子唱一首歌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而西方的成长小说是要塑造出一个少年,一个少年将要成年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自由纯真的人,拥有自由、纯真、人性的人,这是成长小说本质上的理解,一会儿我要稍微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我们再回到成长小说这个基本的概念上来,成长小说关于成长最为精确详细的论述是一个俄国人提出来的,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叫巴赫金。他发明了很多词,有很系统的理论。比如狂欢论,关于叙事的理解不同层面的,关于小说本质性的分类等等,巴赫金他做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的复调小说啊,狂欢啊。现在我们常用的躁动与狂欢等等这些词语其实都是巴赫金总结出来的。他是一个理论巨人,他对于成长小说是最有建树的理论家。我们知道的成长大概就是它与人的教育有关。但是西方的理解有一个限制,就是成人以前的那一部分。我们知道十八岁就有成人仪式了,还要在大学的红旗下宣誓,中国人爱搞这一套。而西方的成人就是你成人以后,这个世界你就有责任了,拥有了自己的权利和去向。在这之前父母作为监护人对你是有责任的,但是成人之后你就是这个社会主体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成人仪式结束了就结束了,家长该怎么管还是怎么管。所以长到三十岁以后父母见到还是喊“宝贝儿”。
身心的经历和遭遇,这都是成长小说要展现的一个内容。巴赫金总结说成长是一个完整的状态,从未成年到成年。巴赫金有句话说“他与世界一同成长”,它自身反映了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这是关于成长小说最核心的论点,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身心上非常具有自由和纯真的孩子,但是他不得不成长为新人,他必须有这样一个历程。我们中国的成长小说如果按照西方的这种逻辑来阐释或成长,我们找不到,在中国就没有,中国有中国式的成长,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套用国外成长小说的那种概念。巴赫金归纳出五种成长小说:纯粹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与年龄保持着联系的循环型成长小说、传记型小说、训谕教育小说、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他分得非常细,而且每一种成长小说都有代表的作品。而要在中国找到比较完美的这样的小说,古代还曾有过,但在今天就特别少。所以我们自己的成长小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湖南卫视有一档节目引用了我们毛主席的一句话叫“天天向上”这是我们对成长的一个预期,一个设定,“天天向上”的过程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过程。无论从身体、精神,还是心智的慢慢健全等。它有一种对成长的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天天向上”,也就是成人对孩子成长的设定,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你要做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你是黑夜里的月亮,鬼影,那都不是好东西,不是好成长。在对待这一代孩子的成长里,我们成长里的目光有非常亲近的溺爱在里面,甚至对他们有所嗔怪。更多的是期盼个和成人的自责,而不是孩子的成长。当我们说到成长的时候,就是成年人的阳光对于未成年的照耀,那种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一种反光,而不是自己发出来的,它是一个没有“主语感觉”的成长。我们对孩子的成长心理上的设定是:你可以成长,但是你要长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向着给定的模子成长,像做月饼一样。所以也就有了让孩子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跟巴赫金所说的“不得不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相比,我们长不出新人,永远都是以前那个样。我们对孩子有这种心理的潜在的规约,于是这些孩子就不得不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人的样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慌了,我们把握不了了。成人就是这样,他把握不了孩子,他就会恐慌,他觉得把握不了世界。所以我们的成长就是在一种消极的、社会公共模式下的成长,永远脱离不了一种自我成长。那么我们有没有欧洲那种模式的成长小说呢?有,我们四大名著里有两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西游记》,这两部小说都有这样的特点。《红楼梦》里从贾宝玉身上就能看到这种成长,一个少年渐渐发育,他对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宇宙、人生都有感应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他一出生就有介绍他是怎么来的,《石头记》,就像《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一样,甚至比《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还要有根据。贾宝玉的成长,我们看到他遭受了很多模塑。包括父母的,贾母的,对他的模塑,还有丫鬟的模塑,要把他模塑成大家希望他成为的样子,将来要撑起这个大家庭。但贾宝玉最终还是成了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他找到了人人都知道的自由。这是一个大命题,一个人生的大命题。鲁迅的《虚亡论》其实非常具有贾宝玉的气质。

我们再看《西游记》,西游记是一个标准的成长小说。十年砍柴他说西游记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作品。孙悟空是一个前青春期的英雄主义的成长,而猪八戒是青春期个人享乐主义的成长。沙僧还没成长就长大了,它是一个后青春期成长主义的自我修炼的过程,所以他在小说中容易被忽略,而孙悟空和猪八戒个性鲜明我们会栩栩如生地记得他们,他们的表情我们脑子里都有。因为我们现在又是一个盛行享乐主义的时代,所以猪八戒成了最重要的明星,八戒他是好男人。在八十年代人们谈到《西游记》想到的是孙悟空,而我们现在想到的是猪八戒。当时有很多网络文学对孙悟空有很好的解释。有一个姓黄的网友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有一种成长叫——悟空》,这个文章非常有意思,《西游记》作为成长小说,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东西,比如说孙悟空自己的成长,他身份的变化,他最开始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时候学了很多东西,在花果山占山称王。还成为美猴王,地方领导啊!然后又闹到了天宫里也想得到一个称号,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官叫弼马温。那些人非常哄他叫他“齐天大圣”。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又一次的满足。而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是西游记里写到的的成人世界,孙悟空就像一个顽皮孩子。接下来就到了归驯,被佛祖压倒在五行山下,最后他似乎也听了大人的话,去给唐僧这样一个和尚当徒弟,成为了“孙行者”,这一下子从精英阶层变成了草根、随从。但是,从小说里可以看到,这个孙行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砺,他战胜了那么多困难,成为了“斗战圣佛”,成长完成。在这个成长过程里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对于孩子的欺骗。这个小说写得非常的生动,无论是佛祖还是观音菩萨,所有的八十一难都是他们设定的,而且,孙悟空他永远都在佛祖的掌心里,他只不过比其他人有勇气,可以在佛祖手心尿尿,但他永远都斗不过佛祖,逃不出大人的手掌。而他的成长过程,从逆反者成为草根,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成为斗战圣佛。整个这个过程达到了我们说的成长小说所需要的天真、自由的人性,孙悟空有猴性,但他的猴性逐渐被消灭,童真被消磨。中国的剧式都是这样的,屏风式的剧式。糖葫芦似的剧式,和西方的小说不一样,我们是从说书开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作为文学,《西游记》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孙悟空哭的时候,他在感情、梦想受到阻挠的时候,孙悟空内心在迷乱,煎熬,这是小说动人的一点。他被师傅、他认为最亲近的人念紧箍咒折磨的时候,他最难受。唐僧就像我们的家长、老师,唐僧他是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下面我们社会的规约力量它是一个凝缩的代表。所以我们说每当孙悟空哭一次的时候,他就向长大靠近了一步。同时,也向他的童真远了一步。人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丢东西,孙悟空一件一件拿到了最势力的东西,也就一件一件丢掉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孙悟空由于虚荣好胜心的引诱,就开始落入俗套,他被管制的成人仪式下,最后终结于成佛。这个小说好在他可以反过来读,反过来读它就具有了成长小说珍贵的品质。它写的是内在个性被迫妥协时,天性之火的自我扑灭,他比西方的成长小说要好很多。《西游记》的成长他还有一个特点,他和我们现在的成长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可以上天入地的宏大的成长小说,他的想象力很厉害,而且它经历了多少代,多少年,从玄奘取经就开始了,民间一直在不断地磨练它,最后到了吴承恩手里。
我们分析完了中国的成长小说,再来分析一下中国现代的成长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十九世纪中上叶的一部作品,十九世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伟大世纪,十九世纪的文学确实是给世界文学立了法。在写《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时马克·吐温其实已经写了一系列的作品,马克·吐温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马克·吐温的经历是这样的,他当过水手,他的家庭也是不那么平静的,后来当水手,在密西西比河上游荡,他们床上有个老船长,他很尊敬他。这个老船长有个爱好,就是爱好文学,老船长对文学的兴趣对他影响很大。马克·吐温当时也不叫马克·吐温,这是他的笔名,他做水手的时候,简称叫“两个标记”也就是测量水深压力的这样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这位老船长以马克·吐温的笔名发表过作品,后来他知道船长要参加一个类似征文比赛的时候,他以老船长为原型写了一个小说,写完后给船长看,船长看了后很生气,因为马克·吐温刚开始写的都是讽刺小说。船长感觉很羞辱了,就不再写了,马克·吐温(借这个名字)又开始写了。后来他当了兵,做了记者,他为了纪念老船长(因为老船长去世了),他就又把这个笔名拿过来,写了一系列旅行的作品,比如《在密西西比河的旧日时光》,《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后来还有《艰苦岁月》《傻子旅行》这样一系列的作品。它为《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出现,在文学创作本身的实践上,积累了足够的丰富的材料。然后来就出现了两个历险记,他的第一个历险记引起了轰动,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面的人物在这个小说里都已经出现。汤姆,后来成为他的小伙伴,而且在写完《汤姆索亚历险记》时他还写了一份手稿,叫《顽童历险记》,当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也是一个好事,发表了可能《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就不能出来了。马克·吐温他特别怕老婆,所有的作品都要给他媳妇看,然后他媳妇用打字机给他打出来,帮他编校,同意发表才可以发表。他媳妇不仅是一审判决,还是终审判决,她说不能发的,就不能发,所以他去世后很多手稿都是被他老婆压着,没发表。后来他写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拿出来后,马上就成为了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这个小说主要是讲哈克和汤姆两个孩子,汤姆在上一部作品《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已经出现过,所以在这里是次要人物。《汤姆索亚历险记》他是借助汤姆这个少年他的逃学,向往自然等等,通过这种东西表达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对美国当时的社会(美国当时是梦想家、冒险家的乐园)的一种批判。汤姆他的本意是做一个海盗,自由自在的,在大海上想抢什么都可以。他想做这样的人,而不是在家里被看着上学的这种。后来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哈克就成为这样的人。这两个孩子,在上部小说里就有了交代,他们在外面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洞,洞里盗贼藏了钱,是一万二千美元。他俩就一人分了一半,一人六千。这孩子还是很有头脑的,他们找到了一个法官,就等于委托这个法官,相当于放债,我把钱放在你这里,但是你每天要给我一美元,相当于利息,起因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哈克贝里·费恩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哈克贝里·费恩这个主人公我们也知道,他和我们中国的小说人物不一样,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野孩子呢,因为在小说里他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他的父亲也不争气,是一个酒鬼,酒鬼加无赖,出了酗酒就是抢钱,不然去河边打渔什么的,总之就是不好好过活,哈克就被一个寡妇收养起来了,这个养母家有个姐姐,这个姐姐叫沃森,他们一起被家长管教,后来就上学,不想上学后就逃学。逃学干什么呢?去学校附近的小树林抽烟,游荡。写到游荡的时候,哈克贝利费恩在马克·吐温的笔下,描述得非常美,包括《汤姆索亚历险记》。记得我当时念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英语课文里面第一课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里面就有关于自然的描述,在密西西比河岸的树林里面,写鸟儿是如何叫,蛐蛐如何叫,水声如何,鸟儿是怎么飞起来的,对自然的描写可以说绘声绘色。野生的状态和孩子内心那种巨大的快乐是一种互应,哈利贝克费恩他有一种逃避教育,逃避成人世界的情绪,他最享受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把校服脱下来,换上他的那些破衣服破裤子,去水边树林子里睡觉,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他不愿意在家里睡觉,这就是哈克贝利费恩。他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一个几乎无亲情、无家教、无礼法的人,一个“三无”孩子。我们中国可不可能这样呢?我们得看得紧紧的。

他在养母家生活的时候,一天他父亲突然找上门来,听说你有六千美元,你给我。哈克贝利费恩很机智,那时候钱已经不在他身边了,他父亲没办法,就把他抓回小树林说,你跟我打渔吧,没事的时候就看着他。他父亲本身也是一个无赖,一个野人,生活得很粗野,他反倒严格要求起儿子说你要像我这样,有时候还把他锁在小木屋里,不给钱就打他,甚至还追杀他。哈克贝利费恩他非常聪明,他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杀现场,或者说他杀现场,他制造了一个被淹死的假象,就逃走了,逃到哪呢?逃到北方,美国当时是南方黑奴制度非常严重,北方就不使用黑奴制度,他想逃到一个码头就上岸,到北方去。但是孩子终究是孩子,他睡过头了,结果船已经飘过了码头,到了一个黑奴制更加严重的地方,一个蓄奴区;而他在养母家沃森姐姐的黑奴叫吉姆也逃出来了,和他相遇,和他一起逃,而且一路上吉姆对他非常照顾,和他说了很多家里的事情,他说他跑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干什么呢?他要把他的妻子儿女从白人那里赎出来,给他们幸福的生活。而且哈克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吉姆都会想办法接济他,哈克在这个时候开始成长,开始真正地成长,对吉姆的认识有一种人性上的认识,吉姆为什么会逃出来呢?吉姆往外跑因为他不想做黑奴了,人们看到吉姆然后就马上悬赏捉拿他,说肯定是他把我们的哈克杀了。吉姆在跑的过程中遇到了哈克,他们就一路跑,可以说是一个艰难险阻的过程,两个人失散过,后来又相遇了。后来还遇到了两个骗子,这两个骗子一个叫王子,一个叫公爵,号称自己是英国最厉害的贵族的亲戚,然后来这里行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美国,文化上崇敬英国、法国、意大利,一听说英国血统,英国人的亲戚来着,当然非常尊敬。他们在行骗的过程中,就把吉姆卖给了一个白人。哈克揭穿了骗子的骗局,他在揭穿这个骗局时,心里也在纠结,这个纠结在小说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他纠结什么呢?他觉得他应该帮助吉姆,吉姆是一个好人,但是他知道帮助吉姆制止所谓的贩卖黑奴,帮助黑奴逃跑触犯当时国家的法律,所以他在国家的法律和人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纠结。如果他是一个大人,他一定站在国家法律那一边,美国人公民法律意识比较强,但是他是一个孩子,一个野孩子,他选择去找被卖的吉姆。找到哪里去了呢?找到了一个农场,那个农场的主人刚好是他的好朋友汤姆的姨父。哈克到农场后他就冒充汤姆,因为汤姆和这个姨夫是没见过面的,他以为真的汤姆来了。哈克在家里就想方设法去救吉姆,逃出白人的手掌。这个时候窘况出现了,真正的汤姆来了!来了怎么办呢?他就到外面截住汤姆,说我已经跟你的姨父姨母说了,我就是汤姆,怎么办呢?哈克想要救吉姆,汤姆这个孩子也很坏,他知道家乡那边很多事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他就不告诉哈克。他觉得好玩,他出来也是为了冒险的,好玩的。他就设计了了一场戏,“好呀好呀!那我就是汤姆的弟弟,”他们就这样骗自己的姨夫。姨父姨母对他们很好,他们就开始计划营救吉姆,营救的过程非常有趣,汤姆知道哈克设计了一个肯定能救出吉姆的办法,他觉得这个事不好玩,他就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很多人都能收到的信,说“吉姆要跑了”。这个农场是集体的看护,他们一定要制止他们逃跑,在逃跑的过程中,吉姆在前面跑,后面整个农场的人都拿着枪在后面追,追着追着就真的开枪了。他们在后面喊,前面跑的都是逃犯,后面砰砰砰开枪,别人都没有中弹,而出这个馊主意的汤姆腿上挨了一枪,抓到以后汤姆就哭着告诉大家,告诉哈克,吉姆其实已经自由了,沃森姐姐去世了,她在遗嘱中说道,吉姆已经自由了。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好玩,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哈克的父亲因为饮酒过度,生活不规律已经死了,哈克的六千美元也还是属于他自己,另加利息,他有钱了。故事到这里按理该结束了,姨妈想要收养这几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很可爱,但收养他们还是和养母一样,让他们变成文明人。哈克贝利他依然不肯,他的梦想是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区过一种自由漂泊的生活。
这个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他不是在写成长,但成长已经非常自然地包含了这个因素,他可以和整个国家的体制叫板。我们的成长小说越写越无奈,以为我们必须屈承,我们的小说越来越多的多余人形象,却没有新人。西方的小说以颓废的姿态多余的姿态其实写的是新人。大人所说的文明人不具备的,但成长小说完成了,完成在哪里?就是现在美国所认同的自己的美国梦,他的美国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健全的心理,自由的心,是这种东西,它成为真正的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融为一体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在反抗、逃避甚至斗争这种现有的国家体制里或者意识形态里获得的真正的精神。这种健全的心灵和自由的心其实最后可以叫做成长的胜利。
马克·吐温曾经自己评价这个小说时说,是健全的心理使畸形的意识吃了败仗。畸形的意识就是指国家的意识形态,最后写的是一种成长的胜利。所以说这部小说难怪海明威会那样说,一切现代美国文学都由这本小说开始,它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它具有一种衍生性。从不同的角度衍生,后来出现的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海明威的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其实都是和我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相关的。如果美国的精神之父在精神论述方面是爱默生的话,那美国现代之父确实就是马克·吐温,可以说后来他所建立的美国梦为后来很多美国作家拷问美国梦提供了依据,你首先得有这个东西才能去拷问去质疑,后来质疑的太多了,几乎都在质疑美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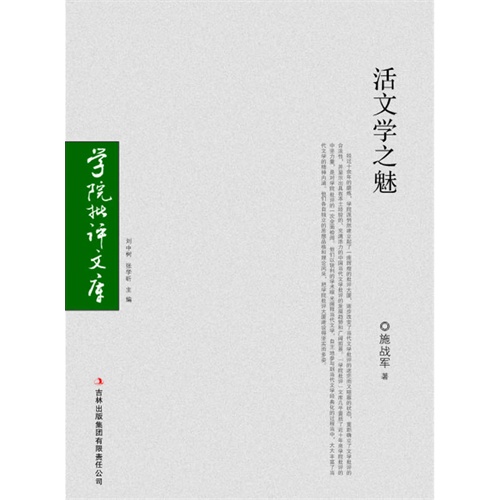
所以我们看无论是美国的电影还是美国的小说,我们中国的小说使劲地在展现一种中国符号,什么旗袍啊,小脚啊,或者最古老的乡土文化。很多中国作家一直在讨论怎么用方言写作,讨论这一类非常浅的问题,但美国的小说一看,无一例外它都有美国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强大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世界精神。我们中国作家的野心就像我们缺少外国作家写野孩子一样,精神没有长好,所以他在世界文学这个天地他永远占据不了主导地位。
我们刚刚评了一届茅盾文学奖,有个著名的作家莫言,他的《蛙》获得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是《蛙》的问题,我们拿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来,《蛙》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有个时候名著就像是一把尺子,一杆秤。《蛙》这部作品确实有他深刻的、很多作家没有想到的东西,他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从他的一个姑姑写起,写一个计划生育接生员的忏悔,说自己有罪,那么多的孩子她接生了,写这个计划生育的生硬性。莫言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早期的马克·吐温作品风格,批判现实主义,尽管他用了很多高妙的手法,以写信的方式来向一个日本作家倾述这种工作和苦闷,最后还用了一个戏剧,它结构那么大胆,那么有创新,但是我们看在这个小说里他缺少对计划生育所指向的那个东西,比如说生命、孩子,他完全是一个缺少的空白的部分,他只说到了这个制度执行者的问题,生命、孩子在哪里?无力气把握,我们已经有那么多人写过少年,如《我是少年酒坛子》一系列这样的小说,但是少年的主体性一直没被赋予,所以他触及得到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却触及不到活鲜的、正在成长中的人的精神,所以这部小说问题在这。即使它已经很好了,好比一棵树,他只写到了树根的部分,仅有树根是不能成长为大树的。我们看到的大树是它的枝丫,比想象中的根细,我们小说本身精神的成长性都不太大,我们看到的大多不是茂密的森林或者大树,看到的大多都是根雕。我们中国的小说家技术都很好,国外的技术马上都学了,今天是尤瑟纳尔明天是菲利浦·罗斯,几乎每个外国作家的风格我们都知道。但国外作家你写得再有技术人家也不学你,中国作家在国外取得很大成就的那一批作家,包括王安忆、莫言在内。我去过外国几家大学的图书馆,确实是有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在里面,而且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性质的分类,写的是社会研究,他是读一个小说来研究中国的社会,而不是文学范畴,事实上外国对中国作品的误解、偏见特别深。他把中国的文学作为报告文学来看,比如说李洱,他的书被译成德文日文意大利文,他写得并不多,但外文版很多,甚至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还把他的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拿来作为礼物送给温家宝,国内很多人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叫做李洱的作家。国外读这种小说读什么呢,他们觉得像学术研讨,中国农村也开始搞选举啦,中国的民主是什么样子,中国是这样来选举的,而看到的不是文学,不是从文学的角度。
而我们看《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部小说在它的人物、故事背后我们所看到的可以说应有尽有:政治、经济、文化、国家体制、区域(南北方)、民族等等。但是这部小说还告诉你:在小说背后最重要的不是政治经济,不是文化也不是所谓的地域、民族、世界,是什么?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精神、风俗和形象。中国有些小说,大家有的甚至故意让汉学家和西方社会注意,而且以不能在大陆出版为荣,那样的一种作家,事实上他是写给西方的社会报告。包括些艾滋病毒的等等,事实上有些人就没被西方出版者发行,他首先就对媒体说;我的书被禁了,真被禁了吗?他往往还没走到那一步,然后就有西方的书商来找他,因为他需要通过它来了解中国社会。所以他首先是把小说当做政治来看,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读巴尔扎克一样,很多人说巴尔扎克是上世纪的一面镜子,说那里面确实有经济政治什么的,我们再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前沿他写道,作家的伟大确实是凌驾于那些政治家经济家之上的。他说:我所写的法国社会不是历史家经济家法学家所写的那个社会,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历史、经济、政治,而我做的是一种风俗史的研究,就是写世道,世道这个东西它和社会的变迁完全不同。他写的都是风俗的东西,风俗的变化就是精神的变化,风俗的结构就是文学的结构。
你们湖南人了不起,沈从文,沈从文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风俗,他非常哀婉于一种风俗,它过去被灰尘掩盖住了,他把风俗上蒙的灰尘擦一遍,就像他在故宫里,突然就投入到瓶瓶罐罐和旧衣服里去了,因为那里面是一种风俗。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把那个时代真正的风俗写出来了,大人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对孩子的启发是什么样的。而我们是通过风俗这个角度来写新象,我们中国作家总是针对某种特定的世界或者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来写,针对一个东西它太短了、太近了,它缺少紧身,不够深远,而新象是什么,我们往往是一种通俗化的小说,我们文学本来死通向一种终极的东西。我们中国作家乐于在中途停下来,比如我们中国作家最厉害的写得最生动的就是血腥的、仇恨的、埋怨的、意淫的,这方面的东西,最厉害了。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它是建立了一种美国精神,一种人类的精神。后来也有垮掉的一代,比方金斯堡,他在质疑一种完全被教条化的自由,说人在这个时候野性完全沦落,美国精神渐渐变成了这样的一种东西,缺少自由创造力,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嚎叫派,垮掉的一代。而海明威那一拨人是迷茫的一代,他这种迷茫是有指挥的,都是在唤醒人获得一种强力,这种强力在文学里面肯定有一种方式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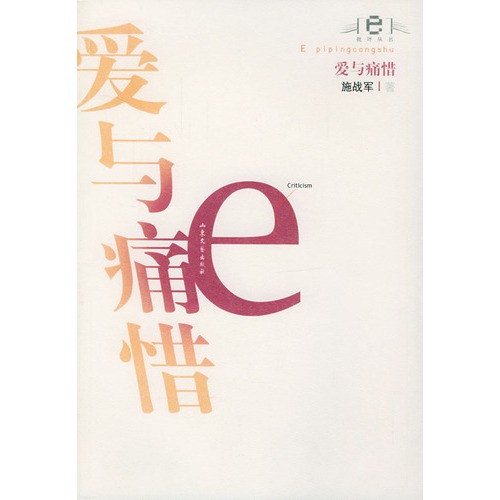
我们说到《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我们也有大概类似的这样的小说,我们分析中国成长小说的特点,我得捡好的说,比如说,杨争光的小说《少年张冲六章》,杨争光是八十年代著名的先锋作家,后来搞影视剧,从《棺材铺》、《双风景》《双旗镇刀客》开始,到后来的《水浒传》编剧,成了大编剧,最后又反过来写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写一个叫张冲的孩子上学,他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有点像,精神气有点像,不愿意上学,淘气,写一口陕西话,文笔很漂亮、简洁,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明清小说。这小说也很有诗意,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就写我们现在中国教育制度对孩子的一种吞噬。小说有些地方写得非常一针见血,他是那个年代积累过来的,他知道文学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地写这个制度,他在反思,写那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如果按照我们简单的思维方式来想象,像想象农民的方式来想象的话,杨争光会写成一个违心人,没办法,所以最后把他写进了监狱。他想写,他有爱心,但他的爱心一直被利用,他读的课文等等都反映出性格所需要的东西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奴性。他写这个孩子也跟邻居家女孩好,坐在墙头看月亮,互相聊的天完全是跑的两匹马。很多地方非常有趣也非常放松,这种小说写到放松不容易,最后是动了刀子把自己送到了监狱。《少年张冲六章》这种小说在中国出现是很珍贵的,尽管很珍贵但这个小说很简单,我们中国作家有个特点,他写作的题材,围绕这个题材的小说太多,而这个小说背后的东西,相关连的甚至是比较远的东西在心里就剔除了,比如我写个东西有拳头那么大,我画个圈,比拳头大一个圈,差不多就行了,或者说画一只手,我们在手的周围找东西,但是你不知道外国作家很多的大作品,他的整个手指头分得非常好。尽管他的细节里我们看不到其他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和我们切身相关。所以杨争光这个作品也是这样,他写到少年张冲的成长史,我们更多的是对孩子的可怜,很少想到自己,我们是什么角色,我们在成长当中起了个什么作用,最后可怜的还是孩子,还是成人首先设定这样一个不错的群体。
西方的法律鉴定,人性鉴定,首先是一个有罪论,你是有缺点的。中国则是一个天然的无罪状态,发言的人,有话语权的人是无罪的,他所看到的肯可能是有罪的,这种出发点就错了,掌握话语权的人,在上面的人首先是他天然正确,也不允许你来怀疑,你怀疑你有罪,从古代就是这样,只有我们中国才会有圣人说,明君说,到今天现在还这样。
(郑小驴根据录音整理)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