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湖南作家网 时间 : 2023-03-30
分享到:
编者按:湖南当代文学史,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青年作家的崛起史。自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文学湘军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崭露头角到黄金时代,再到沉寂突围,继而建立新的格局,这其间,都是一批中青年作家在文坛上横刀立马,铸就了文学湘军的影响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繁荣发展湖南文学,湖南作家网策划了“湖南中青年作家系列访谈”活动,旨在通过与当前创作较为活跃,成绩较为突出的中青年作家对谈,挖掘其写作背后的真实感受和生命体验。在倾听、交谈过程中,再现每位作家的创作之路,从创作背后构建一部关于湖南当代中青年作家的心灵史。
本期作家档案:
秦羽墨,原名陈文双,生于1985年,湖南永州人,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常德市文联。著有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创作与评论》杂志年度作品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湖南青年文学奖。

(秦羽墨)
采写 | 马兵
在有孩子之前的很多年里,秦羽墨像一个隐居在闹市里的人。
住处没装网线,电脑的硬盘里除去电影就只剩下一些文档。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晚上八点以后,他会把手机关机,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书房的墙壁上贴有一张纸条,上写着“时间已至晚八点”。这有点类似于律法里的某种界限划分,八点以后的秦羽墨会捏着劲儿,拍去这个点儿以前留存下的工作、报告、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儿,只留下一个“夜八点的黑土”接管身体,把白天没时间做的阅读和写作一并接手。
当然,这是一种完全理想的状态。
过了三十五岁,俗世和肉体就不会给你那么多自由了。夜里的时间渐渐变得难以掌控。他不再喜欢晚上写作,因为写东西遇到问题的时候,秦羽墨会像耗子一样乱转,在小区里跑上几圈。“深更半夜的,这很不好。”
如果再理想一些,生活的模样应该被涂改成这个样子:
早上起来,阳光照在窗台,写作者在电脑前敲着键盘,或者躺在沙发上看书。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院子,谁也不来关心你,谁也不比你的邻居更了解你。一人独占一半空间,看书写字睡懒觉;老人孩子住在另一边,安安乐乐地过活,彼此隔着庭院相互需要,却互不干涉。
现实逼着我表达
回闪到秦羽墨的童年。
和你我想象中的情况不同,这时的他学习成绩很差,每年期末考试,都是班里的倒数几名。因此,成绩单成了回家挨打的票据。
小学五年级以前,语文一直是心头大患。尤其作文,在某个主题的限定下,绞尽脑汁拼凑字数的体验,实在拧巴。要是把这类成绩再甩到家里的众兄弟中比较,你会发现秦羽墨的作文最差,字也写得最丑。
但也偏偏是他,后来走向了写作的道路。回想起来,秦羽墨自个儿也觉得晕晕乎乎。
非较个真,倒也能分析出一些东西来。据他自述,自己是在一种极度压抑和孤独的环境中长大的。上学时没什么朋友,遇上假期,除了下地干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山上度过。
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毕业,他足足放了七年的羊。
那七年,在山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站在高处,南来北往的风里,传来许多讯息。一个人待久了,脑子里难免会产生种种臆想——表达欲在潜意识层翻涌。
写作道路就这样被动触发了。

(2012年在永州老家)
现实逼着他去表达,去写东西。也正因为如此,秦羽墨写不好命题作文,他的写作完全属于个人的内心世界。
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东西已经触及到他的生理机能。与其说写作是一种精神召唤,不如说是一个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的本能反应。
表达的多了,世俗就容易给你安上各种名头,作家算是其中一个,但秦羽墨拒绝接受这一冠冕。“我觉得我称不上作家,但可以算一个有素养的读者和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写作者不关乎身份,谁都可以当,也不关乎日常状态,更多的是个人意向。
这种虔诚多半还来自对文本的尊重。比如散文,倘若有了一个念头,他会再三酝酿,直至不写不舒服,不把这个念头表达出来就没办法睡觉的时候,他才会落笔。
“散文不能多产,更不可多产。” 秦羽墨的观点与孙犁不谋而合。在所有的文体中,散文对生活的呼应最直接,这是一个过于依赖个人生活的文体。仅从这个角度来说,散文写作对年轻作者很不友好,因为年轻人的经历肯定不如老者来得丰富。但是小说不同,它可以在虚构而真实的世界里多产(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例子),散文多产的作家却很少。
要是有一天,心里没话说了,秦羽墨也就不写了。
他的散文观很鲜明。不管什么题材,什么方法论,它必须是当下的,存在的,介入现实与生命对话的,“我” 必须参与其中。他拒绝,并且反对一切从书里来到书里去、不痛不痒的书斋式写作(不如直接查资料)。在他看来,那类作品,无论好坏,都是一种知识的转移,它不是发现,也不是创造,与文学无关。
写作的“技”
一个念头萌发,成为一个作品的缘起。
这念头像种子,写作者得小心浇水、培护,让它的芽长到一定程度再下笔。浇水、培护的过程,实质就是构思。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组织好了结构才去写一个东西。要是设置好了程序再慢慢往里面塞填充物,那根本不是艺术,而是匠人。当一个想法酝酿到一定程度,书写就会开始跟着感觉走。文字本身的节奏、人物对话都是自然流淌的。这时候,作者本身能够做主的事情实在不多,常常会因为某一句话,而改变了整个故事的走向。
这是写作的意外,也是写作的乐趣。“我们必须遵循文学本身的伦理,而不是机械式地修建房子。”
在他看来,写作的最大快感就是那些不期而遇的句子。当你把事情做完,回头看那些神来之笔,会觉得自己创造了神迹。一个作品要是没有神来之笔,将是枯燥乏味的。
当然,这些是动笔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你得有一定量的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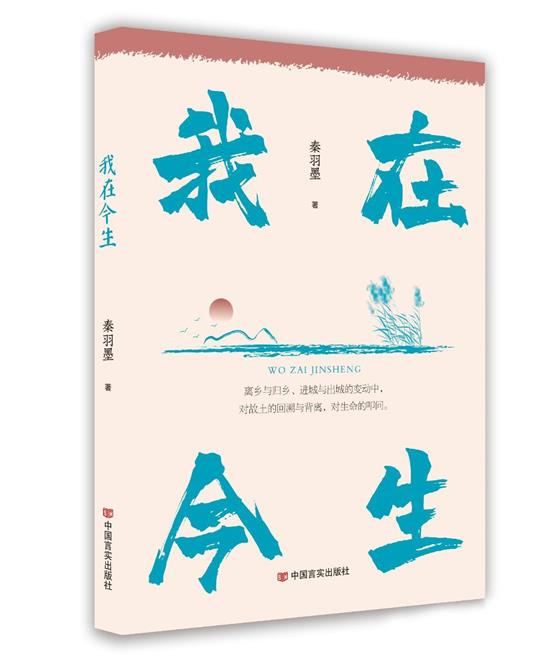
(《我在今生》书影)
一切好的写作都离不开阅读,散文更是如此。这个阅读,不止是简单地看,而是要对比,作纵向和横向的对比: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当下,我们周围世界其他国家的散文写作情况。
然而,现在好多写作者的目光还停留在五四时代。五四确实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但在秦羽墨看来,这里的“大师”更多的涵义在于文化层面,而不是文学层面。五四处于启蒙阶段,各个文体都很不成熟。理性看待,到现在还站得住脚的作家和文本只是少数。
“就散文而言,五四除了提供了文字上的美学,个人以为整体成就并不很高,可我们的写作者,很多人还是拿那些作品作为参考,当代的现实比那个时代复杂得多,我们的散文表达也应该比五四要复杂,在我看来当代很多散文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位置都不会低,这一二十年散文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散文书写蔚为大观。所有的阅读都是为映照自己的写作,在我的写作初期,我会把自己的文章和自己喜欢的作品一起打印出来,从语言到结构,到表达方式,到美学气息,等各方面进行对比。”
要说精神层面,对秦羽墨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沈从文和余华。他几乎读过能读到的这两位作家的所有文字。面临困境的时候,秦羽墨都会想到他们。他们都足够努力,并且创造了自己的奇迹。才华之外,那种与命运的叫板气魄,对其影响深远。文字之外,都非常睿智,看透时代和社会——看似什么都不争,却争着,或者说坚持着最重要的事,丘壑藏在深渊之中。
但他的文字,并没有这两位的影子。就文字本身来说,当代作家里他最喜欢阿乙。给秦羽墨营养最多的则是日本和拉美作家,这个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条,向田邦子、辻村深月、芥川龙之介、三岛等等,马尔克斯就更别说了。
秦羽墨家里设有日本作家和拉美作家的专柜,“日本的文艺美学很符合我的胃口,拉丁美洲人血脉里的巫性气质,天生就适合搞文学。”
蒿村 莫索镇 泥城
莫索镇是一个封闭的城堡,是小说的乌托邦,但并非只存在于虚构当中,只要稍加辨别,你会惊讶于它的似曾相识。当灾难到来之时,那些人跪倒在地,祈求神灵眷顾,他们的姿势“看起来不像在求雨,而是在求饶”,别人眼中的希望,对作恶者而言,是惩罚的刀斧。
——秦羽墨
作品里的许多故事,发生在蒿村、莫索镇、泥城。
就像一个东西的几个侧面,一个人人生的几个阶段,这是三位一体的。蒿村真实存在,是秦羽墨出生的村庄。莫索镇和泥城其实也真实存在,但在小说世界里,更多的成了一种艺术的呈现。秦羽墨提取了看到过的小镇和城市的各种影子。
毫无疑问,这三个地方既是空间上的,村庄、小镇、城市,依次排列,也是时间上的,童年、少年、成年,不断往前推进。它们组成了秦羽墨文学的精神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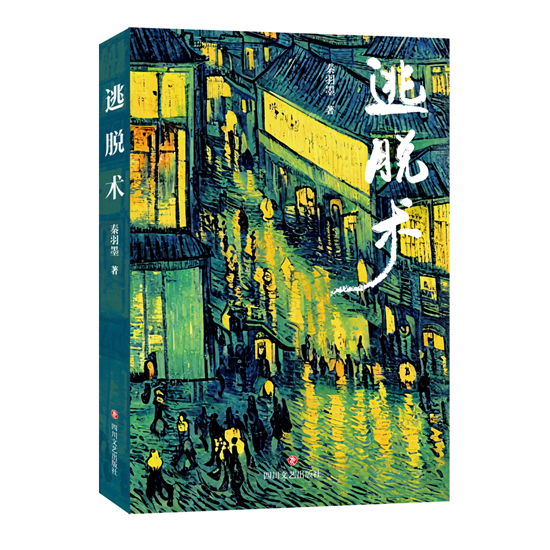
(《逃脱术》书影)
地点在变更,其中的精神内核却始终如一。真实的地点可能没有河流,没有公路,甚至一穷二白没有矿场。这些事物都可以虚构,事实上也确有村庄长着另一番模样:河流流淌而过,公路贯通村镇,里面的人富有得不得了。但有一样东西没有改变,那就是愚昧。不管是儿时生活的小镇,还是眼前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从来没有消除过,只是以更为强大更为隐秘的方式存在,延续至今。所以,笔下的主人公就有了选择的使命。
莫索镇的主人公总想着出逃乡土,泥城的主人公又想在城市中当一个“逃脱者”。他们看起来矛盾,其实仍然是一个东西。莫索镇的人想逃,是对他们生活的环境不满,必须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处境,尽可能地进城去,成为城里人;莫索镇人到了泥城,还想着逃,同样是对自身处境的不满。
有一点不同,也是最重要的不同,莫索镇的人出走是被迫的,是出于物质层面的选择。泥城年轻人的逃离,更多是主动改变,是一种精神上的选择,或者说背叛,带有理想主义气质。
“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但很确定自己不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于是,始终处在内心的动荡之中。”
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问:“如果用一两个词来形容自己,你会怎么选?”
答:“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具体理想,但悲观主义者一定很悲观,而我,二者兼备。“
他一直希望40岁以后,可以不用上班,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机械地上班。但年岁站出来,举着一个接近的数字说,你已经37岁了,还是看不到愿望实现的丁点可能。所以,秦羽墨只能修改这个希望,希望45岁以后可以做到。
“大概率事件是,这个期限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往后推,或许根本不会有那一天,但想法总是要有的嘛。“

(秦羽墨)
鲁迅在遗言里告诫子女,千万别做空头文学家。
这一点秦羽墨举双手赞成。精神上的操守,自己守着就行,以此为业很不合适。要说热爱二字,准确地说,他爱的是自由,而非写作。之所以还在坚持,是因为在写作中勉强能得到一定限度的自由,这小小的自由在他看来弥足珍贵。
”由此,文学本身还是挺好的,它对穷人友好,是一门公平的艺术,只不过我才华有限,努力也不够,属于得过且过的一类。“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