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早蜻蜓 时间 : 2021-12-16
分享到:

(诗人张战。麦麒/摄)
采写丨李婷婷
我们坐在梅溪湖边的一棵桂花树下聊天。桂花一粒粒落在我们头上、肩上、毯子上,桂花在晴天里的香味也是一粒一粒的,而我们的影子在草地上越拉越长……
鸟,一只灰猫,不停落下的金色米粒,都来插嘴,都让我们跑神。张战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此刻跟外界的联系,它们和内心正在发生的碰撞,正是一首诗的生发之处。
以诗为路,完成她的“轻出逃”,以平衡个体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去探寻怎样走出因爱而生的苦。她一直在寻路,一直在打探,并通过诗歌,完成个人独特经验向世界的反射,开辟一条通往他人内心的道路。
“寻路”与“出逃”
以诗为路,去探寻怎样走出我的苦
李婷婷:在你的诗里,“路”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回家的路,出走的路,上山的路,高速公路,风迷路了的路,六十七级台阶的灰麻石路,踩一脚油门被车剪开的路,等着我们走的静悄悄的小路……有时是一种笃定,比如“像捻羊毛绳一样用手捻一条路/不需要规划局批准/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不去罗马”;有时是一种迷惑,比如“风像迷路的孩子”;有时是一种叩问,比如“喇嘛念经/它们排排徊徊/轻轻叩问前面的路”;有时是一种追问,比如“马儿啊马儿/我们能驰骋在什么样的路上”……无论是诗中还是现实生活里,你似乎一直在“寻路”。
张战:我卧室的窗正对着桃花岭,我特别喜欢看山。我发现下了雨之后,烟雾升起来,并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一缕一缕的。于是有了这首诗:像捻羊毛绳一样用手捻一条路……
诗名叫《哭路》。其实是用了一种儿童式的想象,诗里的描写很孩子气。我以这种幼稚的方式去想象我面对一个困境的时候该怎么办。当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哭的时候,人们的追问会像一块块掷过来的石头。结尾我写“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不去罗马”,这其实就是哭的原因之一:我因为跟你们不一样,不被理解,似乎“无路可走”,所以我要自己捻一条路出来。当我看到桃花岭上一缕一缕上升的云汽,我立刻觉察到这两者之间的意象是有相似之处的,这首诗就这样成了。
诗里出现这么多的“路”,我想这是跟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就像你说的,我喜欢在路上,喜欢去找路。『找到一条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潜意识里的一种生命本能,它驱使我不停地在路上,不管这条路是不是对的。有时候你能确定,因为你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有时你不确定,但你也很喜欢在路上的这一过程,喜欢在路上这种生命形式——未知的,不确定的,新的风景和事物。听说有一条新路,我就跃跃欲试,一定要去走走。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身心总处在两极。在阅读时我的身体会很安静,但身体处于运动状态时,比如做一顿饭,细细磨磨洗菜、切菜,比如擦家具上的灰尘、擦地板,比如叠衣服,拉抻衣领和下摆边,用不同方法叠衬衣和叠T恤,这些时候我的心就特别静,特别容易有想法。但心最静的时候是开车在路上时,很专注,眼晴特别尖,路上遇见的某些事物,路上的某些时刻,一下能让你发现被日常习惯所遮蔽的东西。开车上在路上,有时候却又心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空到你完全忘了你在干什么,要到哪里去。那些时候,时间隐身了,它不再在我的耳边嘀嗒嘀嗒响了。
我就是有一次开着车在山里游逛时,突然读懂《彼得·潘》的。我那时突然悟到,为什么虎克船长会怕钟的嘀嗒嘀嗒声,并不是因为那个钟被一条鳄鱼吞进了肚子,而他的一条胳膊就是被这条鳄鱼咬掉,而是钟的嘀嗒嘀嗒象征时间。虎克船长怕老,时间就是将吞噬他的鳄鱼。整个《彼得·潘》的故事都是在讲时间的故事。只有彼得·潘生活在时间之外——但他住的地方叫永无岛!永——无——,这是童话,可是小孩子哪能听得懂!你听懂时就老了!我现在也变成了虎克船长,我也不想听到嘀嗒嘀嗒的声音。
所以每一次出发仿佛一次出逃。也许有那么一会儿,你会忘记时间。而且,每一次出发,总带来新的眼睛、鼻子和耳朵,你有了新的触手。我无数次在路上看到过落日和月亮,每一次看到的感受都不一样。我写了不少月亮诗,也写了不少落日诗。昨天我看着太阳落山,我突然觉得夕阳是一条自噬其尾的金蛇,它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婴儿。
你看,如果我们今天不出来,不坐到这棵桂花树下,我们就见不到这只灰白猫。这猫真是好看啊,它身上的灰色很有意思,你要在白色和黑色之间选一个点来描述它的灰,这灰里是白多一些,黑少一些,还是相反?这一点点灰到底是灰到什么的程度?你要怎么描述?每个人的描述会有怎样的不同。这其间有非常细腻的东西,这就是个人的独特感受,它也会带来一个人独特的语言。
“走出来”给了我们不可预见性,道路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我特别喜欢在野外,从小对空旷的、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有特别的渴望,有些时候,你一定要与大自然保持一种身体接触。

(走在小巷中。麦麒/摄)
李婷婷:对路的迷恋,是否是一种“轻出逃”?通过不断“寻路”,打破一下那种钳进日常中的“秩序感”?一个人的梦想和一个人的现实,这中间是有张力的,你如何平衡这种张力?
张战:对对,就是一种逃逸,逃是为了『轻』——而不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太重了。我们都是带着责任和使命活着的,你对你爱的人负有责任,我觉得这是做为人无可辩驳的本质意义。你尽全力去做。但你往往做得并不好,很多时候你无能为力……
佛家说人生有四苦八苦,我觉得无论是四苦还是八苦,其实只有一苦——爱的苦。爱就会舍不得,放不下,忍不住。有时我也分不清爱与贪之间的区别。生老病死,如果放在自己身上,除了对世间所爱人事舍不得离去,还有不想让你爱的人为你的生老病死受苦。而若你爱的人正在受苦,你眼睁睁看着,不能为他解苦,哪怕减轻,也不能为他背负,我真的做不到看开放下。
我很容易快乐起来,亲人、爱情、朋友、美食、美景……时时感恩,享受,赞美。我也愿意去承担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担负起的苦。你说我有一颗大心脏,有时也就是没心没肺,有时也可以叫做坚忍。女性往往看似脆弱,其实很坚忍的。她们背负,而且她们背负重的东西,往往以『轻』的方式……所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在她们的脸上。但在她们肩膀上,你会看到一块大石头,而且不只一块……女西绪弗斯……
我也反复跟我的孩子们讲,你们的格局一定要大,不管遇到什么,你就想,过十天、一个月再来看这件事,也许就不是事了。但有时候,这话是骗他们的。事实上,你总是在困境之中。我常常感觉,我的心总是揪着。你要知道,爱就是你的羁绊,你的爱越多,你的痛就越多,你就会想要突破。
有一次,我在外面看到一个女孩子,她买了我的诗集,来和我合影。那个女孩子笑容很美,可她的左眼不知为何,眼皮耷拉着,抬不上来。我多想我是仙女啊,是魔女也行,我手指在她耷拉的眼皮轻轻一摸,她的眼皮就抬上去了,那多好啊!但我不能!所以我必须去寻找各种能够走出来的路。
这也是诗歌于我个人的意义。我以诗歌为路,去探寻怎样走出我的愁苦。我既觉得因爱而生的这些苦,我必须承受,且乐意担负,又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些自我的通道。同时,我的路不一定是别人的路,对于别人来说,它不一定有多少用处,我从来不去强化诗歌的“用处”,我也不那么热衷于召唤读者。每个人的路,得自己去找,自己去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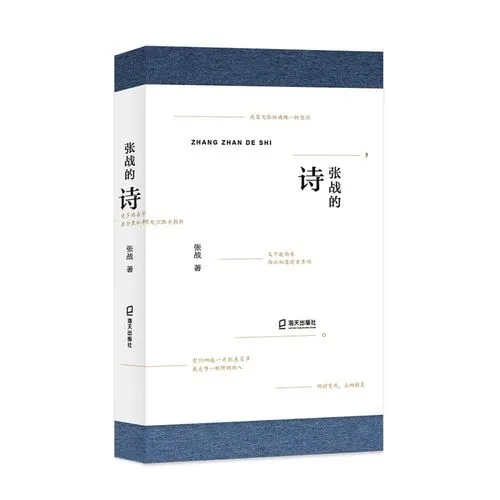
(《张战的诗》海天出版社出版)
“交融”与“建立”
我与社会的交融,一定不会越过我的边界
李婷婷:这样喜欢路,这样喜欢“出走”,是否跟童年那种不断迁徙、一直在路上的成长经验有关?现在回想起来,就你的个人经验,你的最初成长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父母对你的世界观影响最大的地方在哪里?
张战:家庭、父母、童年的生活经验,对我的世界观影响非常大,这是肯定的。父亲长年在野战军里,自小我们一家人就跟着他不断迁徙。我们是没有固定财产的,跟随我们的就是两只皮箱和一口大藤箱。这给我带来的体验是,对于物质,我可以很洒脱,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拔腿就走,即使我有一个小窝了,屋里有很多我心爱的东西,比如满屋子的书等等,但我也可以随时丢下,离开。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父母对我们三个孩子有一种完全的信任和爱意。他们相信你不会变坏,就不会急于去教训、教育你。但很奇怪,我跟我的哥哥、妹妹从小就表现好,至少表面是如此,在外人眼里一直就是“别人家孩子”的那种。
所以从小我们有一种很自由、很宽松、也很愉悦的环境。比如我的妹妹,她总是在追求她的理想,为此抛弃了很多社会评价体系之内认为重要的东西,但我父母都支持她。
父母对我们的态度,让我们在心灵上没有受很多苦,家庭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是在爱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自己也有爱人的能力。
李婷婷:有人说,这一代年轻人是在快速过滤掉青年阶段的,特别快地希望洗掉自己身上的校园气,迅速完成社会化。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的心智往往又不够成熟,造成一种集体的“幼稚的老成”。我一直很看重一个人身上“智慧的天真”,就像你在一首诗的最后一句写:“我的心盛得下所有花朵的盛开/也承得住所有花朵的调寂”,你如何保持身上的这种“智慧的天真”?
张战:生活里,尤其是在信任的人面前,我很乐意让心里的那个小孩探出头来。比如我在和丈夫的相处中,当他描述他儿时的某个场景,我似乎总能看到当时的那个小孩,似乎我当时也在场,似乎我真的看见过。
我熟悉那个小孩,所以喜欢甚至期待那个小孩探出头来。当那个小孩出现,我就跟他打声招呼:“嗨!”然后跟他一起玩。同样,我丈夫也非常愿意拥抱我心里的那个小孩,我们彼此都能安慰好、关照好那个孩子,去跟他做朋友。因为不管你长到多少岁,那个小孩依然是你生命里最真实的部分。
照顾好彼此的儿童情绪,孩子气的那部分得到满足,慢慢地,这种方式就成为一种本能。就像你开车,开久了,车好像变成了你身体的延伸,无论是加油门还是踩刹车,实际上都不需要你大脑去指挥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状态。
个人跟社会去抗争是需要非常的勇敢。但也不难,就是你不能让自己的价值观、生命观完全趋同于社会。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有一个自我的边界。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大方向上,我不可能完全与你背道而驰,在不给我的内在生存造成大的障碍和困惑的基础上,我知道把握住我的边界,多余的我就可以不要了。我跟社会的接触、交融,一定不会越过我的边界。
这其实都只是出于我的本能,一直听从本性的指引。别人可以能说你错过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我保留下了我最想要的部分。

(11月14日上午,由深圳出版集团主办、深圳海天出版社承办的凤凰于飞——《张战的诗》《喊山应》新书联合发布暨分享会在深圳中心书城举行。)
“乐感”与“诗性”
我把一首诗从我心里听出来了
李婷婷:熟悉你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你日常说话的语言就充满诗性和童真。读你的诗,常常会觉得就好像听你在耳边说话,诗的语言和你日常说话的语言是统一的,诗和写诗的人是统一的。
张战:我什么时候写诗,往往并无计划。一种情绪,一种思考也许埋在心里许多年,但触发诗歌出现,也许只在一念。所以我不但写得少,也写得零碎,也写得不够好。但写出来,如果我去探究这首诗的形成过程——它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如何去区分艺术语言和生活语言?我会觉得,不论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你是在把生活中的这种语言素材变成一种诗境。
语言背后是你的生命观。比如惊喜、欣慰、赞赏,你写出的诗歌,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你当下生活的状态。我想,一个人的语言状态就是他的生活状态。
李婷婷:山路、水面、花地、叶片的经脉、桌布和餐盘、小猫的手掌、铺满地面的雪、燕子剪开天空的尾巴……这些看似日常、普通的景物,如何经由你变成了诗?
张战:你看到的这些事物、景象,虽然你都看见了,但不一定能变成诗。就像刚才那只灰白猫咪,它很漂亮,我们都赞叹它的美,但为什么我回去后不一定为它写一首诗?因为它当下没有跟我内心的某种深沉的东西发生相遇、碰撞,或者说发生“核聚变”。
我越来越相信,诗歌根本不是写给别人看的,你写的就是你自己独特的个体生命。但你个体的生命,有点像反光镜,外界的东西通过你反射出来,你又通过文字反射给这个世界。个体的独特性经由你这个人的内心,也许能开辟一条通往别人内心的道路。
我常想,一个人真正的、绝对的孤独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说我爱“独处”,但不能说我是绝对“孤独”的。虽然你独处,但此刻你在读的书,在看的风景,在吃的米饭,都在跟你发生联系,对吧?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棵桂花树下发呆,我看着桂花一粒粒落在我的头上,看着我的影子在草地上越拉越长……这一切都是你跟外界的一种联系。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是切断你所有的感觉器官,你就孤独了。
李婷婷:你的很多诗,尤其是这一两年新写的诗,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旋律感和节奏性,比如很多地方有“反复”和“回旋”,像音乐上的“复调”;有些地方短而快,字就像一粒一粒抛出去的鼓点。这种语言的音乐感是如何发生的?和你平常爱听古典音乐有关系吗?
张战:我以前写诗,更多凭本能,如果说我这两年对诗歌的理解有进步,这个进步就在它的形式上,我更倾向于去真实地听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一个调子,一个节奏。我的诗确实越来越有音乐性,写时不觉得,写完后读起来确实有韵律、节奏、调子,还挺好听。
为什么会这样?冥冥之中是不是与我爱听古典音乐有关,我说不清。这几天我在听舒伯特的《未完成的交响曲》,小克莱伯版的,听得不能自拔。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慢慢觉悟到,这首诗是怎样形成的,其实是我“听”出来的。
有点像昏暗光线里,我用手去慢慢把一个东西捋出来。以前我可能直接把软软的一堆棉花捧出来,现在我觉得这样不够好看,我想把它捋成一串串棉条,捻成细线,再绕一个圈……至于最后到底它会成为怎么样子——再染个色?还是别的什么?我还是不太知道,还是有点听天由命。
所以首先是,我内心天然有一种声音,我听出来了;然后我们写诗时,其实总是会有一个倾诉对象的,这个倾诉对象有时候是“泛指”,有时候是“特指”,有时只是对自己说。我听到了,以诗歌的方式对你把心敞开。你说读到像是听到,我想这也是一个原因。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