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时间 : 2013-12-24
分享到:

小说创作的闲话艺术
聂鑫森
一、从《阅微草堂笔记》谈起
曾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在为《详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清代小说最流行者有三:《石头记》(《红楼梦》的原名之一)、《聊斋志异》及《阅微草堂笔记》是也。《石头记》为全用白话之章回体……《聊斋志异》仿唐代短篇小说刻意求工……《阅微草堂笔记》则用随笔体。”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谈到《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他认为后者“故与《聊斋志异》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已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纪昀,生于1724年,卒于1805年,字晓岚,又字春帆,河北省献县人。他出生于大户人家,三十一岁中进士,任过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四十五岁时,为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传递将被治罪之消息,获“漏言”罪免职并遣戍乌鲁木齐,两年后遇赦召还,复职为编修。他与陆锡熊同任《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大功告成后,又就任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重要职位。他博览群书,腹笥丰厚,为著名的编辑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
《阅微草堂笔记》是他的重要著作,是他五种笔记小说集的总名,共分二十四卷,达一千二百条(篇)。此中近一千篇具备一定的故事性。另外二百条为文物考据、博物知识或单纯议论,故不是小说。
现代女作家柳溪,为纪昀的后人。她曾问过老作家孙犁对蒲松龄、纪昀作品的看法,孙犁很明确地表示他喜欢纪昀的小说。
我们只就这两位小说的艺术手法而论其区别:
《聊斋志异》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在情节集中且起承转合上,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即虚构的成分很大。
而《阅微草堂笔记》,将实录精神引入小说创作领域,不在故事的结构上进行编排、组合,不着意于情节的波澜起伏。
此外,《阅微草堂笔记》在“闲话”上,用力甚多,见性灵、学养、胸襟,看似与小说文本无涉,细细考实,分明与小说文本息息相关,或营造小说的氛围,或展示人物的格调,或升华欲表达之意趣,若即若离,虽远而近。
纪昀的小说,体现了一种自然而少人工斧凿痕迹的状态,使人信服;同时,在貌似平淡中,凸现出一种无技巧的高技巧境界。
纪昀小说中闲话的运用,往往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淳厚的文化气息,使读者得到“故事”之外的文化熏染,铸造了他的小说的文化品格。如《象棋》:
《象经》始见于《庾开府集》,然所言与今法不相符。《太平广记》载棋子为怪事,所言略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为此戏,或有眈之忘寝食者。
景城真武祠未圮时,中一道士酷好此,因其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转隐。一日,从兄方州入所居,见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坐以相待。忽闻窗外喘息声,视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夺一子,力竭并踣也。癖嗜乃至于此!
南人则多嗜弈,亦颇有废时失事者。从兄坦居言:丁卯乡试,见场中有二士,画号板为局,拾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对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
夫消闲遣日,原不妨偶一为之,以此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东坡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荆公诗曰:“战罢两奁收白墨,一枰何处有亏成?”二公皆有胜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践此言,然其言可深思矣。
辛卯冬,有以“八仙对弈图”求题者,画为韩湘、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而铁拐李枕一壶卢(葫芦)睡。余为题曰:“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局中局外两沉吟,犹似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今老矣,自迹平生,亦未能践斯言,盖言则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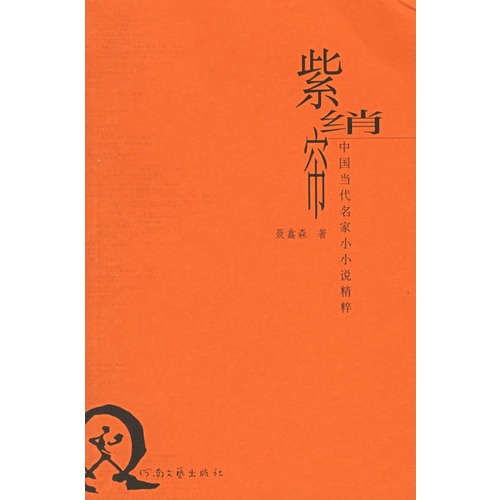
《象棋》的故事、情节在第三段,两个读书人入考场,却以下棋为乐事,摒弃了名利之心,交白卷而出。其余的文字皆为闲话,或说象棋之来源,或说道士的好胜心,或说苏东坡与王安石对胜负的看法却自已未能做到,或写画中八仙下棋的不同姿仪,或说自身人生的检点,都从不同侧面反衬主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是典型的散文体小说的写法。
试说《某千总》,录全文:
乌鲁木齐千总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门求诊,云有夙缘,特相拯也。会一流人高某妇,颇能医,见其方,骇曰:“桂枝下咽,阳盛乃亡。药病相反,乌可轻拭?”力阻之。道士叹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
然高妇用承气汤,竟愈。皆以道士为妄。
余归以后,偶阅邸抄,忽见某以侵蚀屯粮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药毙之,全其首领也。
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相类,岂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欤?
故事:千总患寒病,有道士来诊病,开出处方。高某妇说此方不行,另开方,服之使病者痊愈。后来,千总因侵蚀屯粮被斩首。
闲话:高某妇对道士所下方的看法,“桂枝下咽,阳盛乃亡,药病相反,乌可轻试?”意思是桂枝是热性药,寒疾有虚火会发高烧,服热药催逼,高热退不下,而且生命有危险。高妇所用的是“承气汤”的方子,是作清泻虚火之用,合符病理。作者回京后,读邸报,千总犯法去命,乃联想“道士非常人……”结尾的“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事相类,岂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欤”的议论。
这个小说的“不定点因素”,成为小说行进的推动力,道士从何来?与千总有过什么“夙缘”(过去的关系,但千总并不知)?为什么下一个可让其毙命之方?未遂而去,为什么会叹息“命也夫”?
《阅微草堂笔记》的小说,是典型的随笔体,也就是老作家汪曾祺所称的散文体小说创作。
作为散文体的小说,必有闲话的设置,它虽不直接表现故事和情节,但对故事和情节有着息息相关的观照、辅佐作用。同时,善写闲话的作家,其下力处不在故事与情节,而在闲话的运用,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等老一辈作家。

二、故事、情节和闲话
故事:文学作品中由人物活动构成的生动的情节事件。情节是组成故事的元件。
情节:文学作品中由人物活动过程、人与人关系构成的生活事件,一般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几个部分组成。
英国学者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是这样界定“故事”和“情节”的:
故事: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叙述事情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
比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
“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过度而死了。”这是情节。
闲话呢?是指不直接去描写和表现故事、情节的文字,但却能从不同角度去增加故事和情节的魅力,多侧面展示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性格特征、胸襟气度,而不像有的小说的写法:贴着故事、情节写,贴着人物写,体现的是一种散文化从容而儒雅的格局。
话说闲话艺术的运用与作用。
A、闲话氛围,是为了写人物,即汪曾祺所说的:“氛围即人物”。
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不注重用过多文字写环境(包括天气、地理、民俗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环境也就是一句“那大雪纷纷扬扬下得正紧”,写山神庙也是极简单的。到了《红楼梦》则有很大的改观,在闲话的设置上有许多启迪人的地方。
闲话氛围,其一是隐隐透现强大的社会背景讯息。其二是从氛围中所折射出人物的性格、情感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陈小手》是汪曾祺的小说名篇,不过两千多字,以小说的故事和情节而论,占篇幅不足一半,其余皆可视为闲话。故事和情节为:“联军”团长的太太难产,请陈小手去接生,并接下了一个公子,款待吃饭,给一个二十光洋的包封,然后陈小手上马、告辞。团长掏出枪,从后面一枪把陈小手打下马来。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话碰!”而闲话从一开头的“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直到“陈小手活人多矣”,所占篇幅一半有余。我将这段话照录一遍: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需临时现找。而且一家人都迷信那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我们哪些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承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件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产科医生。
第二段闲话写“陈小手”大名的由来,行医的细致与技艺的精熟。第三段写他骑的马,称为“白马陈小手”。第四段,写陈小手的不屑于世俗,召之即来,而且接生顺利,受人尊敬。
这几段闲话,其实不仅是写氛围,写的是陈小手。同时也为后来的故事和情节埋下了伏线,如团长的太太是随军的,故家中没有其他的女性可充作“抱腰的”,只好陈小手亲自动手,导致团长的愤怒。也写了陈小手的不同世俗,医德高尚,受人敬重,但却遭到团长的暗算,这是一种远距离的反衬。
再说汪曾祺的《受戒》。这一篇最能体现汪老的闲话艺术。全文上万字,但真正的故事和情节是明海的受戒也就是篇末的三千来字。其余的皆是闲话,先写明海故乡的环境、风俗,“他的家乡出和尚”;继写明海出家的荸荠庵的地形、环境,以及这个小庙的几个和尚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再写与之为邻的小英子一家,以及明海与这一家的亲密关系。庙里的和尚,打牌、杀猪、吃肉、唱情歌;明海的拜干娘,与小英子朦朦胧胧的性爱意识……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佛界戒律之外,写的是不“受戒”,是别有的生存态势。而末一段明海的“受戒”,不过是一种走过场,与前面的闲话,形成一种反讽,作者要表现的是所谓的戒律,无法戒定人的生理需要和情感趋向,这是小说的“眼”,即精彩处。
作者在写氛围时,分别展示了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趣味、志向,人物在从容的与故事、情节无涉的闲话中,一个个栩栩如生,这是极高明的。

B、闲话既是一种文化的展示,也同时是细节运用。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在此回的最后一大段,写到一个斗草的场景,其实是闲话,但却在展示“斗草”的文化娱乐中,尽显人物的性格,隐含小说微妙的题旨。
“斗草”,又名“斗百草”,是春天里少男少女们的一种游戏。
那么,“斗草”这种游戏,是怎样进行的呢?
《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斗草”的整个过程:“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子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荳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荳官说:‘从没听见这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
“斗草”这种民间游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亲近自然、和谐自然的美好心境,并由此增长扩大知识面,正如古代圣哲所言“多识虫鱼草木之名”。
这一段闲话,写参加斗草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对爱情充满着绮丽的憧憬,对男性表现了一种渴望亲近,乃至谛结美好姻缘的由衷期待。
命名的对应,阴与阳,男与女,如“观音柳”与“罗汉松”,“君子竹”与“美人蕉”。颜色上的喻示,“红”男“绿”女,如“星星翠”对“月月红”。以花与果,作为男与女的性别符号。“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对应“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牡丹亭》与《琵琶记》都是写爱情的戏剧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香菱。
荳官说:“我有姐妹花。”她答;“我有夫妻蕙。”
香菱虽有婚姻,她却是薛蟠的妾,不是结发夫妻;即便是,薛蟠也无法与之匹配。是反讽。荳官说:“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
两人打闹,香菱弄脏裙子。
贾宝玉出现了,众人皆散,只剩下香菱。他问明情况后,以手中的并蒂菱花说出“并蒂菱”,以对应香菱的“夫妻蕙”。
香菱说:“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瞧这裙子。”
宝玉让袭人送来裙子。袭人离去。
宝玉将夫妻蕙、并蒂菱,好好地埋入一个抠出的坑中。其意发人深思:一、是埋葬他对香菱的微妙情愫与幻想。二也是为香菱的不幸,作一别有用意的处理。香菱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的。
在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中,亦有此种用法。
小说的故事与情节都很简单,是写画家季匋民和果贩叶三的真挚友谊,没有什么奇诡的故事,情节也是碎片式的日常场景,表现的是两个人长久的心心相印和互为欣赏。
此中有一个季匋民作画的场景,一是表现季的高明画技及文化追求,二是表现叶三的别有的鉴赏水平,属于典型的闲话性质,却凸现了两人的情趣与性灵。且录于下:
叶三是从心里喜欢画,他从不瞎评论。季匋民画完了画,钉在墙上,自已负手远看,有时会问叶三:
“好不好?”
“好!”
“好在哪里?”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好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匋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调皮。”
“对!”

接着写到季匋民爱画荷花,他师法谁,有什么笔墨特点。当他画墨荷,画的荷花配上莲蓬时,问叶三:“如何?”
叶三却能实话实说:“四大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季匋民虚怀若谷,重画,再题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着胭脂。”
这一段闲话,见画学见知识,同时也见这两个人的性格,是极好的闲笔。
C、闲话对故事的暗示和对情节的渲染。
闲话尽管不直接描写故事和情节,但决不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乱扯胡说,或炫博学广闻,或只为增加文字的数量。小说的闲话,有一个大体的规范,虽不直接写故事,但对故事行进有一种暗示的作用,对情节的铺排有一种渲染的效果。
以鲁迅的《孔乙已》为例。小说从开头第一节到第三节,便是闲话: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着柜台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底有水没有,又亲自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地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以上为闲话,接下来才真正进入小说本体的叙述:“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第一节的闲话,揭示小说主要人物的活动场景;喝酒主顾的介绍:穿长衫的和短衣帮;酒、盐煮笋、茴香豆、荤菜的价格,勾勒故事的线索。
第二、三节,小说叙述者“我”的处境,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然而他却从另一个可怜人孔乙已身上去找乐趣。同时,牵出掌柜这个人物,他的刻薄、冷酷、重金钱。
D、闲话既可以调整小说叙述的速度,又可改变小说的文体性质。
我们在阅读一些闲话艺术运用得极好的经典小说之后,会惊人地发现,由于闲话在小说各个部分的奇妙使用,使简单的故事变得异彩纷呈,一方面减缓了故事和情节发展的速度,甚至使其暂时停顿因而使故事的长度扩展了,另一方面营造了故事和情节的暗示意味,使其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色上,凸现更多瑰丽风韵。
此外,闲笔的运用,因为它不是直接描述故事和情节,也就减少了故事和情节成为小说主体的常例,使小说的文体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改变了小说的文体性质,使之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使虚构的成分变得微不足道,因而更让人信服其真实性。
汪曾祺的《受戒》,典型地体现了这种风格。
《受戒》的主要故事,是明海和小英子的故事。是明海从出家到受戒的故事。它的长度,也就二、三千字而已。但作者离开主线的“受戒”,写庙中另外一种佛门生活,写另外几个和尚的生存状态,写明海和英子一家的日常生活的场景,都在戒律之外,与“受戒”造成别有意味的反衬。这种闲笔的安置,减缓了故事的行进速度,也增加了故事的丰富性。同时,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话,强化了散文因素,使文体的性质得到了改变。
鲁迅的《故乡》,也是此种写法。
同时,一些名家的散文,因涉及到人物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了小说的文体特色。如朱自清的《背影》,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等等。
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一些作家有意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拉拉扯扯,枝蔓丛生,而处处生情,摇曳多姿。周作人在评论现代作家废名的小说时,说:“他的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汪汪地向前流去。”
早在1940年,汪曾祺就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应该有“散文的美,散文的广度”,应该像风,像流水,“遇到什么都抚摸一下,随时会流连片刻,参差荇菜,左右缭之”,而有“随意说话的自然”(《短篇小说的本质》),到晚年,他更明确地提出了“散文化小说”的概念。
散文化小说,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闲话艺术的纯熟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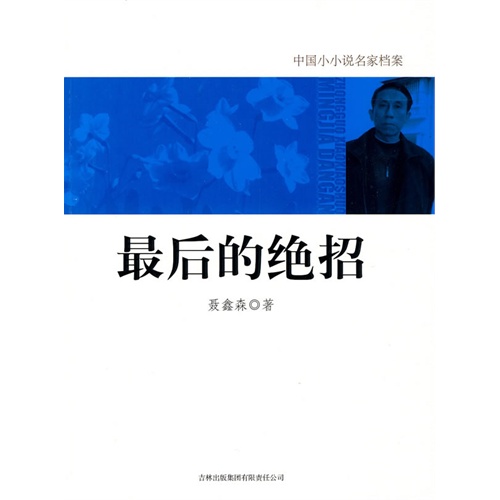
三、儿童视角:散文化小说的一种结构形式
萧红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大套,有各种各样的作者,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聂绀弩《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她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就是一部独特的小说,没有中心情节与主角人物,呼兰小城才是小说的主角。但她以“大地民间”的立场,以散点透视的素描呈现了东北人民原生状的生存状况。吴晓东赞美《呼兰河传》堪与奠定了回忆美学的大师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相比,不仅“为一个代表着古老中国的乡土生存状态的小城在文化学、民族学乃至人类学层面立传”,而且,“预示着一个更深层的母题的生成,即回忆中固有的生命与存在的本质”(《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阈》)。李钧在《乡愁叙事与回忆美学——从《呼兰河传》看萧红的小说学》一文中,谈到这个小说的叙述方式,“而是从儿童视角、女性感受出发,如实地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心记录来,将未加雕饰的民间原生状呈现给读者。”
现在我们来说“儿童视角”的小说创作问题。
所谓“儿童视角”,是指以儿童的眼光探究世界,以儿童的思维呈现情节,以儿童的口吻叙述故事,进而塑造儿童及其他人物的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就《呼兰河传》而言,第一、二章主要是成人视角,第三至第七章为典型的儿童视角,在后五章里既写了祖孙亲情和“我”的家园,也写了“家族以外的人”(失乡的人)的悲惨生活。
王富仁在《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中说:“所有杰出的小说作品中的‘叙述者’都是一个儿童或有类于儿童心灵状态的成年人。”这与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同出而异名,是说伟大的作者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因为“童心”而有了超出常人的发现与创新。“儿童视角”正是这种赤子情怀的表现,具有重要的叙事学功能。
“儿童视角”的特征:
“儿童视角”必然带来叙事的碎片化。这是因为儿童还不具有对世界整体观测和理性分析的能力,因而只可能过分关注细节,另一方面是儿童并不关心时间的线性关系,而对细节的关注恰好是对线性时间的破毁和消解。许多作家对整体故事的切割、倒置,变成碎片化的处理方法,正是这种“童年视角”的生动体现。它使故事向空间层面拓展,呈现出散文化或诗化的结构。
如鲁迅的《故乡》、废名的《桃园》、汪曾祺的《受戒》等。
萧红的《呼兰河传》,时间与事件并置,没有时间秩序、逻辑因果,时间的线性在回忆中被切割、扭曲、停顿甚至倒流。
“儿童视角”感受世界的方式,是物我一体,万法平等的,是直观、和谐、百无禁忌并充满“通感”,因而最具有诗意化的阐发。他们对世界是一种非理性化的认知,这正是文学迥异于自然科学之处,回归文学的本质。
“儿童视角”限定了叙事必须符合儿童的口吻,而儿童表达的重要特点是“自语”和“重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描述一个具象的重要特点就是“重复赋形”。这在文学作品中有着制造文眼、编织活扣的功能,在反复叙述中泄露作者的天机。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