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时间 : 2013-12-17
分享到:

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悖异
——以《边城》为例
王跃文
哈姆莱特的困惑是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如果套用这个句式,我会问:相信作家,还是相信作品,这是个问题。一个文学作品诞生后,这个作品写了什么,作家试图在这个作品中表现什么,作家的创作意图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作家自己有一套解释,文学评论家们有一套解释,读者们也许又有一套解释。对于自己的作品,作家们在论及自己的创作意图时,有时很明确,有时却又很隐晦,令人枉自猜疑,有些甚至成为一段公案。《红楼梦》的创作意图是什么?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写作都是为了是作者的“一把辛酸泪”,可是这作家的辛酸泪到底是什么?到底为谁而流?一直到现在红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有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创作意图的诠释听起来言之凿凿,却又得不到文学评论家们和读者们的认可。在这时,到底是相信作家,还是相信作品?确实这是个问题。
尽管作家们的创作方式和习惯各有不同,但作家在下笔之前,对自己将要写什么,写出的东西表现什么,心中大体是有数的。据说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写作前总要先磨墨数升,然后痛饮美酒,上床蒙头大睡。睡醒之后,铺开纸砚,提笔便写,挥毫立就,写下的文字就不再改一句一字。因为他在磨墨喝酒时已打好腹稿,成竹在胸了。刘绍棠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之一,16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举成名,被称为“神童作家”,他的写作习惯也是先打好腹稿,再列出一个详细的提纲,然后按照写作提纲一气呵成。听人说汪曾祺写作也是事先盯着一个地方久久出神,一字一句打好腹稿,动笔时其实作品已经成了,只不过是把脑子里的稿子用文字写出来而已。汪曾祺曾说:“语言的运用恰如揉面,揉熟了才有劲,写作也就是语言的‘抟弄’。有些人写作时往往写一句、想一句,结果笔下的语言是松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家下笔之前并没有成熟完整的构思。他们写作就像煮茧抽丝。丝未出时,看得见的只有茧。或者像用棉花纺线,手里只有一团棉花,写作就是从这团棉花里把线抽出来。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奥康纳只活了三十九岁,短暂的一生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智血》、《强暴夺魁》)和三十一篇短篇小说,1957年她获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被公认为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她最后是死于红斑狼疮这种病。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奥康纳有一个短篇小说非常有名,我们把这篇小说的名字翻译成《好人难寻》,这被认为是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名篇,故事诡谲阴郁,对人性恶有着惊人的洞察。但奥康纳在动笔之前却从不知自己要写出的究竟是什么。在一篇叫做《短篇写作》的文章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发现。她说当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写些什么。她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走向。她用《善良的乡村人》这篇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善良的乡下人》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小说里有一个名叫乔依(有的译者又把她的名字翻译成“欢姐”,因为joy的意思就是欢乐)的三十来岁的老姑娘,幼年时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她的一条腿被炸断,只好装了一条假肢。乔依有哲学博士学位,自以为看破红尘,非常自负为聪明,没想到一个自称为“善良的乡下人”的推销圣经的年轻人几句甜言蜜语就俘虏了她,把她诱骗到一个谷仓里,调戏她,还拿走了她的眼镜和假腿。乔依的妈妈对此却毫不知情,当她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开时,竟对年轻人做出这样评价:“他肯定是去向后边那些黑人卖圣经了。他头脑真简单,如果我们都这么样,世界就太平多了。”
奥康纳是这么说的:“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女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有条木腿的女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将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总不相信一些作家说的,在他们写作时真的犹如神灵附体,手下的笔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只有写出来之后才知道那是一部怎样的杰作。我想他们在写作时,心里虽然还没有看到那团纺出的线,但用哪一团棉花还是有数的。
假定一个作家在动笔之前,至少心里大致能确定自己要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要表现什么,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什么,自己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一论断成立,那么,我们在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地跟着作家走,按照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诠释那样去理解作品呢?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之后对作品创作动机和创作意图的说明,是不是与他创作出的作品真的一致?我们面对作品时,是应该相信文本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东西,还是相信作家自己所说出来的东西?假如作家所说的创作意图与他的作品本身并不一致,甚而产生了悖异、悖离,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怎么面对这一现象?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又怎么面对这一现象?下面,我想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作家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为例,对作家创作意图与作品的文本之间所产生的游离或悖异现象,从一个作家和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谈一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以此向沈从文先生,向《边城》致敬。

王跃文在毛泽东文学院报告厅为学员授课
沈从文先生是我们公认的文学大师,他的《边城》发表于1934年的1月到4月,分11次在《国文周报》上连载。七十多年来,对于《边城》的评价可谓几经浮沉。虽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就评价《边城》是“一颗千年不磨的珠玉”,但却也遭到了与他同处于一个时代的一些文学理论家、作家的批判。沈从文自己就在《〈边城〉题记》里谈到的:“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茅盾也专门写文章批评过沈从文,说:“炯之先生的文章并无新意,看来也是‘锅中煮粥,同归糜烂’而已”。1948年,郭沫若更写了《斥反动文艺》一文,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和“反动派”,几乎在政治上为沈从文定了性,给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毁灭性的打击。建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对沈从文,对《边城》的评价大多都是从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可想而知,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是一个反面形象,而他的代表作《边城》所得到的,肯定也都是负面评价,比如说他的《边城》“淘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只写出了一个世外桃源,没有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等等。
给沈从文和《边城》翻案,而又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美籍华人夏志清教授1961年初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小说史中,夏志清教授给沈从文写了一个专章,列在第八章,排在鲁迅、茅盾、老舍之后。夏志清评价《边城》是“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中“最完善的代表作”,“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1983年,国内著名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沈从文同志文学成就的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引发对沈从文的重新关注和争论。到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在其小说卷中将鲁迅排在第一,沈从文排在第二,金庸排在第四,而茅盾却被排除在“中国文学大师”之外。1999年,《亚洲周刊》推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以单篇记,《边城》名列第一。而在国外,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先生就说,如果沈从文不在那一年5月去世,1988年沈从文一定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此前沈从文已连续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提名。我们知道,诺奖原则上不颁发给去世的人,而且诺奖一般是在每年12月10日下午颁奖。因为诺贝尔奖金的提供者化学家诺贝尔是1896年12月10日下午去逝的。马悦然说他从1985年就开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翻译他的《从文自传》、《边城》、《长河》,并且说要说中国作家得奖,沈从文头一个就是。而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去世的时间是1988年5月10日。
《边城》共八章,二十一节,五万字一千字左右,只能算一个中篇小说。当然,台湾的文学评论家司马长风也将《边城》称为“世界上最短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不但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们读,文学爱好者读,我想今后我们的后輩子孙还要世世代代读。不但读,还要讨论,争论,沈从文在这篇小说里到底讲了什么?他想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什么?他的创作意图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又似乎都有道理。这是从读者的接受角度解读。那么,即便是从作者自己的角度来看,《边城》的文本本身和沈从文自己对作品创作意图,对作品主题的诠释又是否一致呢?
我们先来看看沈从文为《边城》两次出版写下的新旧两个题记。《边城》正式完成是1934年的4月19日,4月24日写出第一个题记,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署名沈从文。全文太长,我这里只做一些节录。
开头一段:“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这是说自己的身世,是一个军人家庭。沈从文的祖父当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天津大沽提督的裨将,抗击过八国联军。他的六弟沈筌是黄浦军校毕业。沈从文家庭在沈从文小时对他的期许,是成为一个将军。从文14岁就投身行伍,在军队中浪迹湘川黔边境,当过上士,书记,21岁时才离开军队,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考北大没有考上,这才开始文学创作。以沈从文对人生最初的抱负,他应该叫“从武”才对,但他原名沈岳焕,字崇文,后来自己改名叫“从文”,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说,这真的就是命运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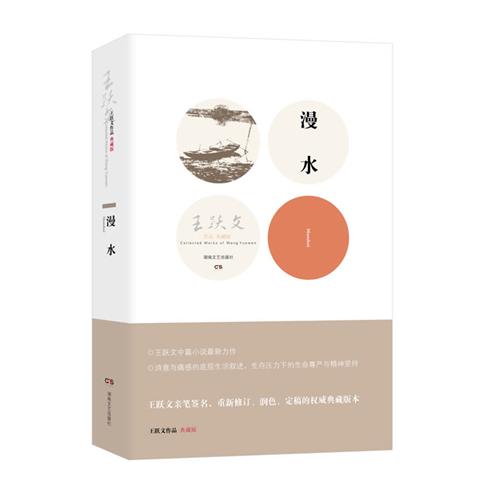
在这篇题记中,沈从文又说:“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沈从文这里说的“这种多数人”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包含了“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文艺爱好者”、“理论家”、“批评家”(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等等在内的“大多数读者”。沈从文说:“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也就是说,在沈从文的心目中,即便他所说的以上“大多数读者”不放弃他的《边城》,作为作者的他,却已把他们放弃了。这是一个作家对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和那些所谓读者的大胆挑战。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沈从文自己一再坚持的“乡下人”的脾气。
那么沈从文的《边城》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呢?沈从文在题记中又说:“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从沈从文的这个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城》创作初衷,是为了给那些“在社会里生活”,“真知道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的人看的。而他在这部作品里要表现的,却是“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很显然,沈从文想要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什么梦幻或者理想。而且,这种现实是“忧虑”,是“不可知的命运”。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沈从文的这句话:“不可知的命运”。这种人在命运前的无力感,孤独感,悲剧性的宿命感,我认为是沈从文作品中,尤其是《边城》中要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边城》的新题记发表于1948年。此时离《边城》的初版已有14年了。他的新题记很短,我全文录下:
“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新题记主要是追述《边城》产生的过程和缘由。前面是写自己对《边城》故事所发生的自然环境茶峒的了解过程,后面写翠翠的原型由来及作品的整个写作过程。大家注意,这个新题记,一共只有343个字,却有两处写到悲哀、悲伤。一次是回忆在微雨中离开茶峒,“闻杜鹃极悲哀”,一次是因为母亲在书出版前一年去世,所以“书出版时心里充满悲伤。”而且《边城》的写作过程,第一章写出后曾因为入冬返湘看望母亲而中断,来回四十天。回来后接着写。关于这一次返湘,也促生了沈从文的一部散文集《湘行散记》。这部散文集共十一篇,主要创作于1933年后的几年,作品描述这次乘船返乡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特别值得提出来的同样是,许多人看到了《湘行散记》中的牧歌情调,却忽略了作品中不时隐现的悲凉与忧伤。这一点与人们对《边城》的解读极其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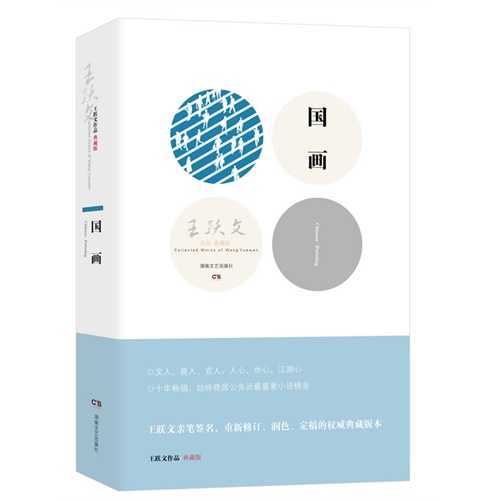
沈从文还有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理解《边城》真正的创作意图也很有帮助。这就是沈从文于1942年创作的散文《水云》。这篇散文主要以对白和独白的方式,写生命中的“偶然”和“神性”。我认为这篇散文中隐藏着沈从文创作的很多秘密。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又一次提到了《边城》人物的形成过程:“因此每天大清早,就在院落中一个红木八条腿小小方桌上,放下一叠白纸,一面让细碎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中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见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这里,沈从文又一次提到了“到处是不凑巧”,这种命运的“不凑巧”,也就是命运的“偶然性”,必然会给人生中的“善”带来难免的悲剧。
不仅仅是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对《边城》有误读。沈从文自己对《边城》创作意图的说明到后来也了变化。《边城》初版后两年,即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沈从文写了一个代序,其中写到《边城》。“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这个“代序”里,作者还在前面写道:“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这里所说的“人性”,其实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从他众多的作品来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沈从文要在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即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人的自然发展与需求不受阻碍而表现出来的特性。应该说,这两段话主导了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对沈从文作品尤其是对《边城》主题的解读。给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定位为“田园牧歌”,“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歌颂”就成了公认的一种评价。
同样,沈从文自己在散文《水云》中也提到“牧歌”一词,沈从文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水云》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离《边城》发表已经有8年。8 年中,我们可以想见一定有很多文学评论家把沈从文的《边城》称为“牧歌”,沈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对《边城》“牧歌”的评价。作者一方面自傲,一方面自卑。因而,当“牧歌”评价听多了,自己也从了。这一评价同样影响到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他也把《边城》称为“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中“最完善的代表作”。沈从文的弟子,被公认为是沈从文的衣钵传人的汪曾祺也写过一篇文章《读〈边城〉》。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可见,汪曾祺对他的老师沈从文《边城》的解读也认为这是一篇“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是一首“美”的颂歌。
从1934年《边城》发表后,沈从文先后写下的两个题记,到后来沈从文的《从文小说习作代序》及《水云》,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自己对《边城》的创作意图的自我说明出现了游离和悖异。那么,《边城》到底是如同沈从文在他最早的题记中所说,是要写出“将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虑,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还是如同他后来所说的,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或者是要构建一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小”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我觉得,答案还是应该在作品中,在文本中去寻找。
文本这个词是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兹在他的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来的,用来指称文学著作,他的意图是想把文学作品从作者个人心理和历史文化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瑞恰兹长期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担任教授,1930年曾到清华大学来讲过学,死于1980年。他是新批评派的主要构建者。我们知道新批评派主要强调通过细读文本来解读作品。文学研究有四个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新批评是独重作品文本的。
下面我想谈谈通过阅读《边城》这一文本,我对沈从文小说《边城》主题的理解。当然,我不是学者,也没有受过新批评研究方法的训练,但是,我确实细读了《边城》。我认为,《边城》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最早的题记中所说的:是写人类命运的不可知性,在这种不可知的命运笼罩下,人对命运的不可把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与悲哀。我认为,《边城》的主题,无论是作者的有意还是无意,也无论作者曾经怎么说,后来又怎么说,悲哀或者悲凉是作品的基调,而人在这种悲哀与悲凉中的的坚韧尽责的生命形式,又包含着作者对人生的大悲悯,写出了人的生命的大庄严。

我这样说,一定遭到众多人的反驳。因为不仅是一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们已经把《边城》定位为唯美的田园乌托邦和乡土抒情诗。沈从文自己都说了,他要写的是“表现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构建一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小”的“人性”的希腊小庙。常言道,解铃还得系铃人。作家自己的作品,难道作家自己还没有发言权,还不了解吗?
诚然,《边城》确实以一支如梦似幻的笔营造了在他记忆中的湘西世界的自然美和人性美,可以说,写得晶莹澄澈,圆融剔透,充满诗意的纯净美丽。这个名叫做茶峒的小山城,“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都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调和”,这是远景。近景是这样的,镜头渐渐往近处移:“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
《边城》中的人物,人性,也是写得美到极致。翠翠的形象性情是这样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也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般,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的外祖父呢,这位老摆渡人“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仿佛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摆渡从不要钱,“渡头本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他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中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那个!”。在河街上,他随处把酒葫芦里的酒慷慨的倒给水手喝,以致于船总顺顺要把他的酒葫芦收起,另外喊人给他送回家。买肉,屠户“照例不愿接钱。”而老船夫宁可不买,也不愿占一厘一毫的便宜。交钱时,他嘱咐屠户数一数,“屠户照例不理会他,一手钱哗的往竹筒口丢去。”其他的人,比如船总顺顺,也是个慷慨而能救人之急的人。“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游学文墨人,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他将水上赚来的钱,为扶危济困而“洒脱散去”。“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肥鸭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爷爷的老朋友杨马兵对翠翠的照顾也感人至深。这位钟情于翠翠的母亲,但又被拒绝的杨马兵最终义不容辞的接过照顾翠翠的任务:“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他在翠翠的外祖父去世后,把自己的马匹托营上人照料,自己同翠翠做伴,把一个一个日子过下去。“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

沈从文这样写道:“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感和羞耻的城里人还可信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是那么浑厚——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评价的:“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园晨阳的空气里。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求,他们的心力都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中写得最美的还是翠翠的爱情。汪曾祺说:“翠翠的爱情是一串梦”。
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作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年纪较长的,如他们爸爸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年幼的则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可是翠翠喜欢的是二老傩送,但顺顺却偏偏派人给大老天保做媒。中寨王团总给女儿说亲,用碾坊作陪嫁,看中的又偏偏是二老。大老天保因同弟弟争翠翠受挫,心中失意,坐船到茨滩去,不幸淹死。二老因哥哥死去,又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加之父亲对娶翠翠有些反对,赌气坐船下了桃源。受到顺顺父子的误会,又为翠翠终身大事操心的老船夫终于心力交瘁,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死去了。这样,翠翠的爱情竟成了一个悲剧。
可以说,沈从文把《边城》里的自然与人情写得无一不美,无一不善。按理,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理想世界,可是为什么故事里的人物命运却无一不带有悲剧色彩,无一不是在孤独与悲哀中默默承担着命运所给予的,而且仍然认真坚忍地继续活下去呢?翠翠母亲的命运是一个悲剧,翠翠的爱情是一个悲剧,天保傩送的命运也是悲剧,祖父的命运是一个悲剧,连带小说里次要的角色,杨总兵,如吊脚楼上唱歌的妓女,其生活无一不是那么孤独凄凉。在《边城》里,人人相爱,却人人孤独。《边城》里风情人物至美至善,然而谁又能逃脱这种无常的命运的悲凉?我认为,无论沈从文自己后来怎么解释《边城》的创作意图,我从《边城》里最能够得到共鸣的,却是《边城》所表现出的人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簸弄下的无奈与悲哀,以及尽管如此,却依然各尽生命之理的人生庄严。这是使《边城》不仅仅是希腊小庙,是田园牧歌,是乡土抒情诗,而是有更深更大人生内蕴的真正所在。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觉得在《边城》还有一个隐性的重要的角色,就是死亡。《边城》中作为背景的两个人物,翠翠的爸爸妈妈,在故事还没有开始就死了。他们为什么必然要死,沈从文实在写得语焉不详。翠翠母亲爱上一个军人,老船夫不同意。那么,他们本可以逃走。然而他们不逃,却选择先后殉情。其原因,是“一个违悖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他们的死亡阴影一直笼罩着全篇,并直接影响到翠翠的命运,甚而,翠翠命运就是她死去母亲悲剧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复。这几乎就是一种宿命!老船夫怕这个,一直竭尽全力小心翼翼保护翠翠不要重蹈母亲覆辙,但是逃无可逃,悲剧命运还是在翠翠身上降临了。这也使得《边城》尽管写得风物明丽,人性皆善,然而从一开始,却又无一不笼罩在一种悲凉哀伤的氛围里。接着又有一处提到死亡。翠翠第一次进城去看端午划龙船,爷爷独自先离开了,翠翠站在河边等爷爷,却听到两个水手在谈论吊脚楼里唱歌的妓女,讲到这个妓女的身世:“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忽儿”。这里,仿佛又为后来爷爷的死去埋下一个伏笔。小说还多处写到翠翠和爷爷谈论到死。比如那个夏天的夜晚,有月亮,翠翠和爷爷坐在屋外石头上看星星,吹芦管,听虫鸣。(顺便讲一句,沈从文在《边城》里写虫鸣、鸟鸣,虫子的气味写得极好,是文字中的极品。)这时“翠翠俨然极认真的想了一下,就说:‘爷爷,我一定不走。可是,你会不会走?你会不会被一个人抓到别处去?’祖父不作声了,他想到被死亡抓走那一类事情。 老船夫打量着自己被死亡抓走以后的情形,痴痴的看望天南角上一颗星子,心想:‘七月八月天上方有流星,人也会在七月八月死去吧?’又想起白日在河街上同大老谈话的经过,想起中寨人陪嫁的那座碾坊,想起二老,想起一大堆事情,心中有点儿乱”。 再后来就是天保坐船在茨滩掉到水里“淹坏”了,然后是一个雷雨夜,伴随着白塔的倒圮,爷爷的死。
《边城》一共写到五个人的死亡。这使得小说从头至尾都笼罩在一层死亡阴影的哀伤中。尽管沈从文尽力淡化死亡的恐怖。在他笔下,连死亡都是那么富于诗意与美,且大多是为了爱,为了爱的幻灭和悲伤。这么多死亡,然而我们可以说并没有一个凶手。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凶手,那就只有无常的命运,也就是沈从文自己讲的“偶然”和“不凑巧”。

也有人要问,既然作者写的是人类无法挣脱的命运悲剧,为什么作者又要把小说里的环境人物写得那么美,那么善,然后又让他们无一不陷入命运那只无常之手,无一不各自带着内心的伤痛与悲哀去生活?这正是这个作品最成功之处。如果我们认可鲁迅先生说的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那么,在沈从文笔下,越是美好善良的生命,越应该得到幸福而实在没有理由得不到幸福生命,恰恰不但不幸福,反而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流的挟裹下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安命坚忍,在悲剧中不失态,不放弃,仍然尽职尽责地活下去。这使得《边城》更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唯其如此,才更显得命运的无常与残酷。
《边城》人物命运悲剧的根源,不少文学评论家有过阐述。凌宇教授就认为主要还是社会原因,是封建宗法社会由财产悬殊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份悬殊和心理隔膜,也因为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但有些悲剧的成因,又实在只是因为偶然。比如天保被水淹坏,这应该说不上是什么社会因素。而这又是造成翠翠悲剧命运,造成老船夫死亡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沈从文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小说中已经借老船夫说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不公平!说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在《边城》里,最沉重的,是作者写出了人物对自己命运不可知、不可把握的孤独、无奈与悲凉。但尽管命运无从把握,不论命运如何凄苦悲凉,他们却并不自暴自弃,而是依顺着命运的轨道,坚忍而又尽责地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这里面又体现了人生的一种大勇气,大庄严。正是这一点,我觉得《边城》写出了人类普遍的永恒命运。这使《边城》的主题上升到一个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永恒命题。
那么,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作家自己在阐释自己文本的时候前后相互矛盾,文本的本身似乎也出现了矛盾。其实,这种作家对自己文本阐释与文本本身的不全等,甚而游离,悖异,在文学创作中是很正常,也是很常见的事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作家对自己本人个性情感把握和表达的不确定性,也有作家对社会因素反映的不确定性。很多文学评论家喜欢把作家的作品看成是作家个性和情感的表现,作家的写作不过在于尽量成功地给自己的个性情感找到一个合适的“客观对应物”。 20世纪英国诗人艾略特在论文《哈姆雷特》一文中说:“以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建筑一个‘客观对应物’;换言之,寻找一组物体,一种境遇,一连串事件,它们将成为那种特定情感的表示式;这样,那些一定会在感觉经验中终止的外部行为一经作出,就立即会引起情感”。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我读了艾略特这段话后很纠结。因为我的英文水平很差,无法读原文。艾略特这段话的本意其实是说真正成功的作品是与作家个人的个性情感无关的。他还有一句名言,他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但是,我怎么读艾略特前面说的那段话,总觉得他恰恰在说一个作家个性情感与他作品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作品是作家为自己个性情感的表现而寻找的一个“客观对应物”。无论如何客观,它又必然是“对应”的。新批评派还有一个术语,叫“意图谬见”。所谓“意图”,就是指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内心的动机、构思和计划,它与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他的看法,他动笔的原因等有着明显的关联。这个术语是新批评派学者维姆萨特提出来的。维姆萨特明确指出:“就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来说,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对《边城》的解读,就不用去管沈从文先生自己对作品创作意图的诠释,是否前后矛盾,是否与文本所表现的一致了。其实,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作品永远大于思想,作品也永远大于作者。而作为文学作品,或者文本本身的多义性,隐喻性,它所表现出的悖论、朦胧和张力,恰恰正是文学最大的魅力。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