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湖南作家网 时间 : 2024-11-27
分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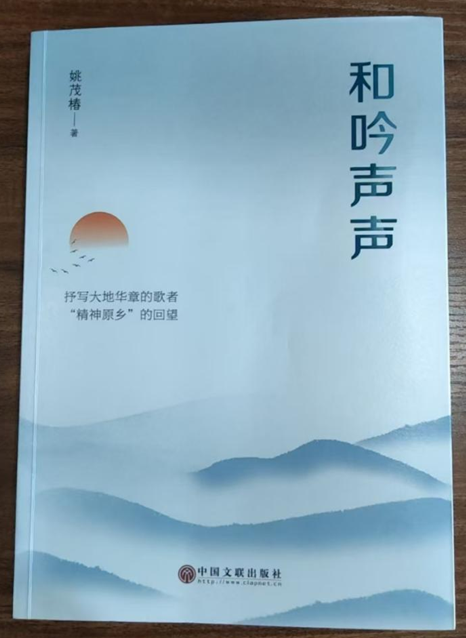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姚茂椿,男,侗族,湖南新晃人,居长沙。在《民族文学》《文艺报》《诗刊》《诗选刊》《湖南文学》《湘江文艺》《飞天》《散文百家》等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散文集《苍山血脉》(湖南人民出版社);诗集《放飞》(民族出版社)。散文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部分诗文获奖并入选一些选本。
作品节选:
群山前方
阳光在细雨洗涤后,更加透亮。群山前方,是向往中的湘江源。清新的风迎面而来,夹杂田野庄稼的气息。经过山间公路的颠簸,汽车往峡谷幽翠处钻去,像在一幅宽大的风景画里慢慢收笔,轻轻落在一丛浓绿的深处。
潺潺水声耳畔低语。向导表示,湘江源在不远处。顺着水流,我把目光移向眼前的山上。
这在当地百姓一直叫野狗岭的地方,水成了最洁净的生命体,成为一些思索充盈的源头。当我面对湘江,在湘江旁繁忙地工作生活,随学习和经历增多,对自然与人生的许多褒抑是非,就有些感悟及溯源之想。湘江送来许多思绪,它的源头令我向往,充满神秘。
黄土路变成水泥路,大家放开呼吸,汽车渐至平稳,车轮下的尘沫早已消停。车驻。移步。无数笑语。流水露出天然的面目,没有杂质,无比鲜亮。水面太小,倒映不下两边的山,任由一些草木摇头晃脑进来,打个照面。遇有花朵盛开,水面定将荡开一圈圈羞涩的涟漪。源头还有不短距离。小溪按捺不住,有如童年般的活泼,有着脆亮的嗓子,欢快的声响伴着它朝石板坡下奔去。
溯源需要上坡。在木质栈道,踏一级一级的台阶。栈道规整,弯曲,上扬,顾及游者的舒适。皮鞋摩擦在栈道上,毫无以前踏木梯的感觉,稳扎,无声,踏板明显不是精细加工的南方成群的松杉。木质佳美,据说来得很远。栈道与水流上下并行,依地势保持忽近忽远、忽高忽低的距离。一些湿气穿过水声,软软地拍在栏杆上。小鸟的脆鸣被融进水里,水声便在小鸟的翅膀上腾起,朝山顶几丛翠竹飞去。
野狗岭有了湘江源的大名后,人们叫唤它的时候少了,但说到湘江,说到它作为源头从这里流出的水需要大家珍爱的时候却多了。它成了无数湘人的诗和远方。踏栈道踩石阶的步行,到达不了那个孕育湘江的神秘泉眼,石壁耸立,我只能在一袭薄纱般的天泉瀑布前伫立。仰望水瀑,想象它有怎样的神秘身影和动人的神情。
我从大湘西到长沙叫了几十年的母亲河,源自这里。岁月奔流,对母亲河的感恩之情愈来愈深。在星城第一次看到湘江,就有久违的亲情在心中涌动。喝了湘江水,那些甜蜜和牵挂,就一滴滴一丝丝融入血液和灵魂。湘江的养育,使一个懵懂青年一步步成长,感受时代阳光,增添生命力量。
感念湘江源头天赐,紫良瑶乡更名为湘江源瑶乡,影响和名声与日俱增。我从县到省先期是做民族方面工作,办公室同事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白族,当然少不了瑶族。我们在这备受关心,自己也初心明晰。短短几年,我工作足迹遍及三湘四水的民族州县。就瑶乡而言,最难到达的湘东龙渣、湘中小沙江虎形山,我都随领导住过。遗憾的是,地处湘南的紫良瑶乡,一直没有前往。某年参加多部门调研,行程万里,我前后去了许多民族村寨。住在高寒的虎形山茅坳瑶乡,贫困景象令人忍不住流泪。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艰苦经历成为我调研思考履职的宝贵财富。
在长沙的最初日子里,我喜欢将目光长久停留在宽阔坦荡的湘江水面。无论远在城郊还是近在咫尺,都有满怀的激越和畅想。凝视橘子洲头和第一师范,有大河奔流前指点江山的感慨。红色基因得以不断觉醒。在湘西塔卧的一栋小木楼前,我对红色队伍的成长壮大,有了深切的感受。八九十年前黑色恐怖下的湘江上游,红军差一点遭遇了灭顶之灾,但鲜血没有白流。它见证了湘江两岸的黑暗与光明,一个日益美好的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信念坚定的断肠明志的红军师长,军民鱼水情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又为我们的信仰注入了新的情怀和元素。它使我懂得湘江的水流再大走得再远,不能忘记它的源头和起点,不能忘记经历过的艰难和挫折,不能忘记前行中的无数溪沟和支流。
栈道之上,又是沿山的台阶。不知哪来的石块,为拜谒湘江源的游人作着沉稳的铺垫。人随石阶上升,水沿沟谷下去。各怀心思,各得所愿。有些情怀浓郁的水,迷恋源头的山色,在某个水域流连再三,才缓慢前行。而前方,它会遇见也会迎来一条又一条溪河,从最初毫不起眼的小小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它清冽,很甜,另一些加入者,同样清且甜。当然,排除不了某个沟谷刚刚遇到大雨,流水冲刷腐朽的树叶,浑噩的黑泥黄土,翻滚而来。也排除不了人为的违反自然的后果,筑堤挖沙,生活污染,直排劳动生产与工厂企业的废水。湘江源及各支流上游的纯净,经中游下游的污浊,最终的水会不成样子。流动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遗憾。近些年的治理保护,才使湘江又焕发青春。
天泉瀑布的脆响令人诧异,那些响声在山间渺茫的静里,显得不太真实,可它们在耳畔的萦绕却实实在在。来自源头,跃下山崖,瀑布在人的意念里突然有了硬汉的感觉,不停鼓动出心中的力量。湘江源的山那边,是九嶷山。《山海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万山朝九嶷,中华始祖舜帝,寄托着人们的情思和敬仰。湘水源头,增添了人文始祖的神采和厚重。浩荡湘江,养育了两岸的生灵,浇灌着百姓的生活。湘江的养育和启迪,让无数英雄和人文之星升起。远的不说,近现代中国的星空里,湖湘的群英最为灿烂。湘江源,由此更让我们景仰。我听天泉水瀑,听到了它们的团结奋勇,听到了它们的自强不息,听到了它们的无私奉献。
有的人远道而来,一路拥挤喧嚣,找几个网红角度留影,发数张照片,收获一些点赞,满足虚荣心。有的人神情严肃,一路思索多美的生态,如何保护。有的人面向源头,想到的比那些水下行后的千万种命运,还会更多。我没有脱离红尘,张着仰望的翅膀,从不很洁净的下游溯源而来。我喜爱湘江源的一切,在一个最接近流水的地方,弯腰伸出期待的手,捧一些泉水喝喝。手一点点升高,一滴两滴清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滴下,亮目。手捧着水接近嘴唇,竟能感到亲切。柔甜的感觉从舌尖开始,接着凉爽畅快,一股舒坦从心里涌上面颊,直至整个头部。第二捧水,在口腔分泌出凉甜,从喉部美美地往下滋润。第三捧水竟然理性起来,味觉让开,将清甜绵甜爽甜抽出无数的丝,一点点游进意识,编织出内心感觉上的荣幸和满足。
一棵几株联体并排的树,伸向栈道,似乎向我们揭示什么。是能够成为一条大江源头的水,被赋予了某种神力,才有这样神奇的展示?是湘江的频频回望,还是无数期待的注入,才使靠近中华始祖的山岭,孕育奇迹?这是一棵斜出横向生长的杉树,在它横卧的身躯上,竟然向上长出六七株子树。小杉沐浴阳光,在几只蝴蝶的环绕下神采自足,虽然它们还没高壮,但足以令我们浮想联翩。
喝过湘江源头水,看过天泉瀑布,返程感到很不过瘾,不能在烙上精神印记之外带走源头的一点什么。蓝色背景里的洁白云彩不能带走,舒适甜润的空气不能带走,婉转绚丽的鸟语不能带走。同伴魔术般摸出个空矿泉水瓶,近乎得意地在我眼前晃动,我立即羡慕他的先见。他立刻笑容满面,把一个同样的瓶子,递到我的手上。
我们焕发童心,迈腿跑向湘江源的水流。
老 家
老家离我出生地扶罗的寨街,有几十里山路。那地方叫鸭塘。传说一口水塘,在耀眼阳光下,有金鸭子熠熠生辉地出没。老家由此得名。鸭塘界上有个读书的地方,父亲读过几年书,解放后有了工作的机会,离开了老家。
我不在老家出生、长大,却对老家感受特别。它的意义,或许与当前离乡的新城市人有所不同。回老家的经历,沿途景色,一些小小事件及由此而生的忧乐和思绪,有的越来越清晰,就像近在眼前,而有的已经迷迷茫茫,变得非常遥远。
大弯界
穿过扶罗街头的公路,沿洒溪往上游方向走,经过几个小寨,坝子越来越窄。溪两岸的山脉不断升高,收拢的地方,是个从没干涸过的湖泊。这叫龙塘的湖泊不大,周围草木阴森,四季雾气缭绕。前人对它不甚了解,加之敬畏,留下许多有如巫蛊的传说。
关于龙塘的来历有几个版本。一说,一个穷苦的看牛娃发现一大蔸头天割了第二天又有的青草,被财主逼迫,挖开草蔸,出现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宝贝。随之,一股大水喷出,淹没了一切,出现了龙塘。很久以来,这里的塘边水中,死过一些无辜的人。被水淹的、砍柴被树砸的、从悬崖上摔下的,不一而足。传得更神的故事,是一个整日懵懂的人,在塘边见到两条大鱼,大如家里晒谷的晒席,比双人床还大。他陷入无边的恐惧,不久病亡。还有人说,塘里的龙,在某年的大水时,随水走了,有人看见在汹涌的洒溪,一条大蛇很凶猛地冲出去了。
我回老家,一般不从龙塘边的小路往上走。一直走着的花阶路,在离龙塘几百米的地方,在还看不到塘和水时,就逐步抬升,朝着侗语叫擒恰的高山爬去。擒恰的坡很陡,但花阶一路向阳,两旁的枞树杉木高大繁茂,鸟声悠扬。我看见很美的大鸟,如红中带绿、斑斓的锦鸡,就在林丛树间,悠闲从容地飞落腾挪。它们艳丽的羽毛,展开时能让人感到,什么叫惊艳。在你期待清晰却未明了之间,啪啪几声,它们拍翅一飞,躲了起来。
上到擒恰坡顶,进入大弯界的地域。我不知大弯村有几个寨子,走在离山脊很近的花阶上,就像穿行在深深的密林中。有的地方,头顶是大树斜伸出的枝桠,夏天的中午也不见太阳。想在这截路看到周边的木楼,真是有点异想天开。兴奋盎然走着,清凉,幽静,一阵风把你带入一个古木参天的三岔路口。而每次经过这里,我都真切感到,一些令人害怕的气息,在周围一阵一阵地漫延。
一棵黑黑的古树,像一年四季没晒过多少太阳的老人,略露病态。除了天生的脸黑手黑脚黑,却还非常神秘地枝繁叶茂,叶子浓密得像那个老人从上到下罩着一袭黑衫。黑衫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你悄悄伸出的想象,由于害怕,不敢深入。收回小心翼翼的目光,我发现树边不远的地方,摆着几块方正的石头。石头前,数根香棍工工整整插在泥巴里,还有几团红烛和黄草纸燃烧过后留下的痕迹。
我知道,这是人们敬神摆土地的地方。当地,人们习惯将土地神称为土地菩萨,源于人们不懂得世界上几个著名的宗教,更不懂得教内的级别、分工。
也就是那棵古树,让人想起一些传说,我甚至有时认为,它至少成了精,是一棵彻头彻尾的树精,吓唬着天昏地暗或夜晚途经的行人。当然,它更有可能是棵树神,它从上至下直至树根,都神性十足,用许多细节展示着是神的更大可能性。一方面,它边上有土地神,我了解凡是神都是好的,神的群体只有保佑人、帮助人的,起码我没听说过神害过好人。另一方面,我在树干上不止一次看到过人们对它的崇敬和信任。在一人高的地方,常常贴着一些红纸,上面写着几行毛笔、钢笔字,意思是请过往的亲戚朋友知道并拜托转告,某月某日,大弯寨或某某寨某某家,有如某某老人八十大寿等好事,请亲友到时来喝酒,或老人不想烦劳大家,只请哪几处至亲,感谢其他亲友并请谅解,等等。我有次看见,上面贴的内容是:“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哭夜郎,过往行人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下面还署名并说明缘由。我当时出于极大的好意,一连帮那家念了几次。我仔细端详,古树遒劲的树枝,像粗壮的手臂,能给需要帮助的人送上无穷的力量。树枝和树干的交接处,就像在人的腋窝的地方,缠着不少红绸,我想,那应是人们对它在一些方面显灵的还愿和谢意吧。
快到大弯坡,必然像遇到一个亲切的老人一样,遇到一眼清泉。走了一个多小时,肯定口干舌燥,来到泉水边,一种心想事成的满足或者对善解人意者的感动会油然而生。泉水叮咚响,一股甜蜜早已沁人心脾。但是别忙,不要着急喝水,先得轻轻拨开,在你之前喝过水的人留下的井标。
那些井标,多是一些黄茅青草,打着一个很好看的结。我非常感谢前人留下的这个习俗,它提示人们几层意思,说明这个水喝过啦,没有问题;也提醒过往的人,不要弄脏了,后面经过的人还要喝呐。有的人性急,撩几点水在边上洗手,手干净了就捧起水喝。更多的人会看到边上,那几丛早有准备的青树,你只需摘两片巴掌大的树叶,轻轻一洗,合拢一卷,就成了一个环保的真正绿色的杯子。捧着树叶杯,慢慢喝下汩汩冒出的甘泉,那种感觉,怎一个美字说得。
上得大弯坡,总感到有亮堂堂的阳光,突然降临。大坡绵延,小路平坦,眼前稍大的树木不多。向阳的坡面,虽然比较陡,但几乎全被开挖成旱土。路的两旁,曾给我带来许多快乐。杜鹃花开的季节,东一丛西一丛的大红、桃红,在风中摇曳,特别的惹眼,摘几朵干净的放入嘴里,那种清新和淡淡的甜味,至今难忘。野果成熟的时候,路旁更令人兴奋的是又红又密的东西,侗话叫览产,我不知它是不是汉语中的山楂。那东西有点甜,水不多,助消化。吃过览产,就可以到坡中间的凉亭躲太阳、歇凉了。
鸭 塘
十四岁那年我读初二,即将迈入高中,步入青春的行列。在向扶罗中学团组织递交申请书后,老师安排两个同学与我一起,去老家了解家庭历史情况。老师开过介绍信,我与同学在一个周末的中午出发了。这是在没有大人带路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寻路走向老家。
在几十公里人烟稀少、断断续续的花阶路上,我们有说有笑。同学对名声在外的鸭塘,心驰神往。
过了大弯,就要下坡。花阶边上,一股激流在不知疲倦地响亮地鸣唱。由于河床陡峭,叫做陡溪,可在一些地方,被人们写作斗溪。
下过陡溪,弯弯曲曲走过一些田园,经过几个鸟语花香的小寨,我们看见晏家寨前横跨溪上的风雨桥。那桥不大,比较简陋,没有雕梁画栋,但已具备遮风挡雨的功能。运气好时,碰上一两个老婆婆或将成老人的嬢嬢,在桥头笑容满面卖粑卖粉。现在的晏家乡当时是个行政村,由于相对开阔,居住比较集中,那时设有如供销社的代销店一样的几个代办点,而最有规模、最热闹的,是村里的小学。我在县里工作时,曾在该校调研青少年工作。
往前,又要上一个大坡。当时从县城来的公路,途经鱼市公社,窄、陡、拐弯抹角地经过那个坡,才通到晏家。爬坡时,为缩短路程,我们走近乎笔直的小路,几次穿过大家称为马路的公路。上了坡,汗淋淋地沿着马路往前,不断曲折地往前,将到达一个叫血饱屯的地方。每到这里,我的耳边老是响起先辈们与封建官兵、与强盗土匪厮杀的声音。眼前模糊,树林草丛中似乎还有晃动的身影、斑斑的血泪。拐过小弯,走出这一段阴郁,前方,才姗姗现出一个并不怎么宽敞的山口。
“鸭塘界到了!”我手朝前一指,同学几个一起兴奋。
几颗苍劲大树,屹立山口。它们像一排威武雄壮的士兵,守护着方圆数里的安宁,保卫着一个个山寨。它们也像几位日思夜盼的老人,焦急地等待在那里,迎接远方的客人和外出归来的亲人。
站在大树边,远远望去,鸭塘的上寨中寨下寨连成一片。建房的坡不很高,依山建造的木楼从下往上,一层一层地上升。深色的屋,上面覆盖着黑瓦,浅白的翘檐非常醒目。人家不很多,但迎面张望的木楼很齐整,远远就给人一种团结的印象。
想必,同学已经知道,对面的那些木楼里,全是姚姓人家。侗族的聚族而居,延续得很好。一般地说,山间的村寨,基本都是宗亲家族不乱,同姓之间辈分不乱。这里虽不像南部侗乡,按宗族家族建有鼓楼,族群标志很外在看得到,但这里选屋场建房时,也会有些规矩边界。人们在侗寨出生,就会在百花盛开的民俗中,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在新晃乡间,姚姓之间不能通婚,不知是哪一代留下的规矩。而县内人口最多的杨姓,划分了如七甲杨、八甲杨等群体,不同甲之间却可以结婚。由此一来,就有了很多有意思的生活生态。如寨中某家在杨姓或吴姓的寨子娶个媳妇,那这个寨和那个寨,任何一家之间都成了姻亲。人们按联姻人的辈分,严格区分长辈和晚辈。贵客临门,被亲人们争抢着招待,若在一些大的寨子,一天到黑都会吃饭喝酒不赢。
我老家的屋,在上寨比较中间的地方。上辈勤劳,建的屋比较大,一栋主屋,还有一栋同样较大较高的厢房。
我与同学的到来,让祖父、叔祖父等老人非常高兴。他们竭尽所能招待我和客人,然后连夜去干部家开出证明。
风水树 母女井
从鸭塘界朝鸭塘寨子望过去,在上寨和中寨之间的一片古树,非常醒目。那些参天古木,一棵棵随便站着,从山脚到山腰,树冠几乎连成一片。记得很小时,祖母去世,我走走停停磨磨蹭蹭,轮流在父亲和舅舅们的背上,赶往老家。那一条山路,实在漫长,紧走慢走,都见不到几栋房子,看不到几个人。小脚磨出了泡,痛进了心里。到达鸭塘界的大树下,坐在草丛上,远望那一群老树,我感到了自己小的无奈。寨子上,吊丧的唢呐声,无力的锣鼓声,稀疏的鞭炮声,远远地传来。寨上的人看见了我们在界界上的身影。有人迎过来了,我却看不见,只感到那一群古树表情凝重,离我们越来越近。
古树林为鸭塘增添了美。夏天枝叶葱绿,引来方圆很远的大鸟,一群群地飞来。中午歇凉休息,叽叽喳喳说过不休,或居高临下地高歌。有的把窝搭在上面,早出晚归,不知所往。有的喜欢热闹,听见树下有人经过,就拖腔拉调,来那么几句,不知所云。到了枫叶红了的季节,几棵枫树尤其显眼。枫叶一丛一丛的,在高处摇晃,像醉了酒的脸一样。偶尔会有小手大的枫叶,飘洒于风中,像一些红色的小鸟,飞在树间。
这个老树群落规模不小,每一株都高大俊美,生命力又及其旺盛,引来了不少人的拜访。有的考察,有的拍照,有的甚至想把它们中的某一棵买走。高龄几百年,矗立数十米,这些树成了这块土地上最老的主人,也成了鸭塘寨一股不散的灵魂。它们历经风雨往天空撑起的,不仅是赏心悦目的美,而是族群生命生生不息的风景。它们古老的身躯,展示着侗乡山寨的厚重。政府林业部门,已将它们登记造册,列为永久保护。
鸭塘上寨还有个有特色的地方,那就是水井。一股开口不小的泉水,从未干涸。泉眼下,一口透明的不太深的井,荡漾着每户人家清晨挑回饮用的甘泉。井口溢出的下方,是又一口规模稍大稍深的水井,井中的水,用于人们每天洗菜洗衣洗物。这像个吕字的上下两口井,当地文化人有的称为套井,我却称它为母女井。因为它,多年演绎着侗乡母女生活的生态。
有勤劳的母亲,也就有勤快的女儿。母女井旁,每天来得最多的,是寨上人家的女人。不论母亲女儿,还是婆婆媳妇,一日两餐三餐,生活中的洗东洗西,都需要在井边操持。大集体的时候,男女一样出工,稍有休息,男人们上山砍柴,女人们洗菜做饭。田土分开各自生产后,女人更是井旁的勤快人。一年365天,没人离得开这两口水井。
从母女井流出的水,沿着下行的水沟,灌溉寨里的稻田,还充实了几个水塘。外面嫁来的女人,从晚辈变成长辈,这里嫁出去的姑娘,也在延续山寨的血脉。母女井,从来都没有干涸。
母女井离我家老屋不远,两百米左右。在老屋二十多年前毁于寨上火灾后,我近年清明节回乡挂亲,不想看那荒凉的屋场,就喜欢一回回从母女井边经过。头些年寨上人说干旱下雨井水很差,要求在更高的地方新开水源,为每家每户牵去自来水。我们在外的人积极捐助,圆满做成了这件好事。母女井被冷落了。而近年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在家的人减少,自来水没人管护,水差了,水管不通了。从而,母女井又被重视,又有人饮用了。
望着母女井水,我身边淳朴沉默的山寨,突然变得开朗起来。由井而生的小溪,是寨子的一个肢体,叮咚缠绵的声音像老人的叙述,潺潺不休的语言在慢慢流动。它与古树上的鸟鸣,相映成趣。好像鸟鸣是寨子的歌声,一会儿在树丛,一会儿在木楼,从这里到那里,不停地飞翔。山寨的女人没有闲暇打扮,没有工夫唱歌抒情,这母女井的水,就扭动着腰肢,把她们的婀娜,淋漓尽致地模仿再现。
老家黑得发亮涂满桐油的木楼,因风水树变得有更有精神。一些男人走出大山,心中装着挺拔的古树,就有了顽强和力量。母女井的水在人们血液中流淌,常唤起他们的乡情和亲情。
老家,被拥在怀里装在心里,随我们走南闯北。在游子梦中,它是一片定格的风景。游子用回忆,将它一次次重温。一栋楼,一棵树,一口井,都会让人怀念老家。一段生活,一些场景,一些细节,总在眼前挥之不去。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