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钱江晚报 | 张瑾华 时间 : 2020-08-10
分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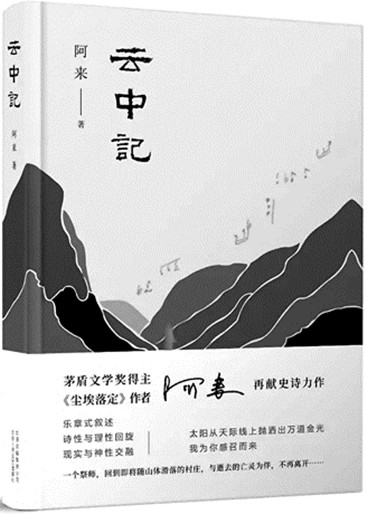
《云中记》的最后,阿来写下这两行字:“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2018年国庆假期完稿。”
一本被视为“安魂曲”的书,就像一块静静伫立的纪念碑。
阿来曾剖白这段“失语”的时光,“我自己产生一种警惕,觉得在汶川地震的重大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得很清楚,但有一天我肯定会动笔。”
《云中记》的时间线,以乡村祭师阿巴离开移民村,回到震后已荒芜无人的“云中村”告慰亡灵的第一天开始,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到第七天,到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直到“云中村”因山体滑坡彻底消失的那一天为止。
“云中村”是一个藏族的古老乡村,“云中村”又可能是在中国的任何一处土地上,一个个中国古老村庄的缩影。
春风悦读盛典举行的前几天,钱江晚报记者与阿来进行了对话。
年度白金图书奖得主:阿来
十年后的安魂曲
一场对消逝和重建的慰藉
十年后的触动
三个月就写完初稿
钱江晚报(以下简称钱报):“云中村”是完全虚构的吗,它有一个现实原型,还是无数村庄的浓缩符号?
阿来:在四川泯江周边,这样的村很多,那种村落很典型。说到这个“云中村”,我还是希望一个作家写小说,笔下的地理、自然环境要有真实感,不然就是空洞的。不要虚化小说的空间,不然现实感会降低。
钱报:书中的主角“非物质文化”阿巴,他从一个半吊子的祭师,学习做一个真正的祭师,最后选择与云中村一起消失。为什么在十年的思索与沉淀之后,关于这场大地震,您最后给读者的“第一人物”是阿巴?“阿巴”有没有原型呢?
阿来:我住在成都。当年地震,我算是个有限度的参与者。作为志愿者,也在灾区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想,我写什么呢?怎么写?灾后是漫长的恢复重建。重建更多不是物质层面的,更多的是心理问题,那种修复很难被看见。
阿巴是有原型的。有一天,搞摄影的朋友扔了张照片给我。他说,某某村你知道吗?地质调查说最后要消失,所以就移民了。那个村有个人,每年到祭奠亡灵的时节,他就回去。照片上的人,那身祭师的行头很特别。这件事对我有触动,但那时我也没多想。
我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写了一半,忽然地震来了,我就离开书桌,去当志愿者。等我回来重新捡起写作,突然警报一拉,已经十周年了。我一下就不行了,当时几乎不能控制,泪流满面。于是我锁了门,至少有半个小时放任自己的情感,然后就开始写这个小说。写的时候,完全是历历在目,太熟太熟了,那气味那场景。三个月,初稿就写完了。
文学不应仅关注人与人的关系
钱报:您是个特别亲近自然的人,这些年是一直生活在都市吗,还是总有时间在大自然里游走?
阿来:我每年写作时间并不长,经常就是去走走。我们在城市里穿行,城市生活是自然而然的,真正不了解的,是乡村的问题。到哪儿我都说要看看农村,乡村确实需要我们特地去加以关注。只有乡村真正发生了变化、转变,农民从意识、从文化上,成为现代人,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完成。
每年我有大量时间旅行,去乡村,也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文学是一直有自然在的,比如山水诗。张岱写《陶庵梦忆》《西湖寻梦》,一半是自然一半是人文。我非常喜欢杭州,过去十多年,要么春天要么秋天,每年会在杭州住上个把月,西湖周边都走遍了。
今天的中国文学,太拘泥于人跟人的关系了。但除了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关系里头。跟植物,跟动物,跟一座山一条江,都对我们有情感的抚慰。当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得不到抚慰时,就在自然中寻找。
钱报:您在书中还提到一种人跟语言环境有关的关系,比如阿巴们使用汉语时,就呈现出另一个形态来。
阿来:少数民族语言里,有那种书里写的诚恳庄重的语言。至少这是一个文化现象,我呈现出来了。但不急于下结论,更重要是客观的呈现。
我觉得对作家来说,还有个跟语言的关系。网络时代到来,写作越来越粗放,但是大部分看不出有2000年的历史传承,是一种粗俗的文字。雅正的语言是我喜欢的。人家能做那么好,我们做不好,很丢人。长江黄河的感觉去哪儿了?一个作家对中国历史、对文化有敬意,首先应该集中在语言的体现上。
钱报:《云中记》不仅是一本关于灾难的安魂曲,也是一本关于“文明冲突”的厚重之书,书中处处有古老习俗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您写地震,同时也写了一个乡村的百年发展史和消亡史。
阿来:我内心有一个东西。中国文学有个小毛病,过于追求某种思想性。我认为文学的深度是情感。过于追求主题的东西时,会造成文本的单薄。
当下的世界,小到一个城市,一条街,一条胡同都在变化中。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产生,会发生冲突,要靠人的生活去表达出来。消失的在消失,生长的在生长,不然地球早装不下了。
我更愿意审美不过于绝望
钱报:书中还说到了记住和遗忘这一对矛盾。移民村的人们普遍认为,要不了一百年,云中村会彻底被忘记。您曾说过,“我并不认为所有旧的东西都应该保存下来”,但万物又都有发生和消亡的时候。您是怎么看待遗忘和记住的?
阿来:我觉得遗忘才是一个主调。可能遗忘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滤,能不能把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传承下来。人们说革故鼎新,我以为对旧事物的留恋,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的留恋,而是一种集体的谎言,或者说一种表演,一种下意识。
我觉得梭罗已经很装了。
钱报:《云中记》主要是彰显灾难后重建家园和修复心灵,善与美的力量是全书的主要支点。您是否有意地将人性比较负面的东西进行了隐晦的处理?
阿来:我想从《诗经》开始,世界文学主要还是向善向美,我个人经验中,更愿意审美,不过于绝望,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更喜欢写真善美的东西。虽然人性有各种暗恶之处,但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世界变好。如果真善美都熄灭了,那地球是不是得灭亡了?
我们说的“解构”并不是最终之道,解构是拆房子了。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建构呢?我觉得建构更重要。拆完了不管了,还是不行。
人生中,我们还是希望得到一点慰藉。就我个人来说,文学是救赎之道,能从中得到一点安慰。不然我们不就成了我们鄙视的“那些人”了吗?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