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张雪云 时间 : 2020-06-01
分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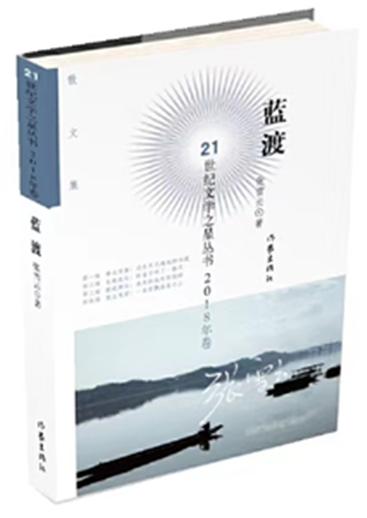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张雪云,女,苗族,湖南沅陵人,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教书十余年,目前供职于省作协毛泽东文学院。有多篇文学作品发表于各报刊杂志,散文集《蓝渡》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内容简介:
散文集《蓝渡》以土地河流为经,苍生万物为纬,勾勒出一幅大湘西的浮云山川画图。全书分为四个小辑——席水而居,泊在月光遍地的水途;长歌起处,阳雀子叫了一整天;踮起脚尖,未央的流年刚刚好;微尘苍茫,一朵雪飘落在云上。作者在字里行间,突显出一种浓重的乡土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表达,通过深沉的凝望,悠长的讲述,具着个人独有的感念和意蕴。作者从个体生命的遇见与思虑中,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一种民族的情结,一种文化的清丽,呈现出在时代快速发展,乡村振兴过程中,对于乡村人物骨子里坚韧精神的敬重,乡村风物沧桑之美的固守,彰显乡村与城市碰撞融合的生存哲学,心灵轨迹与生命感悟互为一体的智性力量。作者清婉朴实的叙述,幽深灵泛的思考,烟雨薇汀的忧愁,似水般淙淙流淌,若山般静穆厚实,很细腻,很温暖,很质朴,既有局部的精细,又有整体的豁达。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渡口,或者,就是蓝渡。
与一条河流有关
(序言)
叶 梅
湘西多河,它们的美丽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沅江、沱江、酉水,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以至于他在清澈见底的河上荡漾而爱意绵绵,“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人们从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得知了湘西那些知名的河,如今我们又从一个湘西女子的描述中知道了一条小溪,一条叫蓝溪的小溪。蓝溪相对那些知名的河流,就像环绕大树而去的藤蔓,小巧但更加缠结多情,也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使人神往倾心。
苗族女子张雪云自幼生长于湘西凤凰山下、蓝溪河畔,她出生的年代正是改革开放初始的1979年,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沅陵县的一所中学从教多年,对读书写作的喜爱成为她最为钟情的选择,渐次在多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迄今为止,她的作品多是从她的家乡蓝溪生发开来,感受土地深处的呼吸,体现湘西的脉动与温度,在平常事物与百姓生活之中感悟到诸多深意,以小见大,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回望乡村,以对土地与自然的真诚守望而发声,让心灵中的蓝溪所奔往的大江大河长流不息。同时,她描绘着有血有肉、阳光明媚又风雨交加、幸福与痛苦同在的乡村地理,勾勒出湘西特别的雾朦胧、湿漉漉的山水,以及在那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魂魄。她的散文集《蓝渡》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其中的篇章均是她这些年的精心之作,正是试图以土地河流为经,以苍生万物为纬,织一幅湘西地域风情的图画,从中显示出其独有的乡土精神和自我意识,表达她对乡村人物骨子里坚忍精神的敬重和承接,对湘西乡村独特风物的呵护,对乡村与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碰撞融合及变迁的若干个人思考。
显然,一抹乡愁是这幅图画的底色,张雪云以一个灵秀女性的敏感细腻,兼之深情灵动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描绘着自己的家乡。“从蓝溪出发,溯游而下,相望千年的沅江、酉水两岸,如一幅水墨画卷,亦如一部典藏的古籍善本,徐徐展开,直扑人眼,不用泼墨点染,也不用刻意着色,左岸右水的原貌便成了画中的经典,氤氲出一片清澈的云水与禅心。”她小时候日夜相守的蓝溪看着她长大,蓝溪很蓝,她的童年也很蓝。虽然后来的日子里走过许多的路,看过许多的风景,但仍然一遍遍梦回那山清水秀、林木繁茂、鱼鲜笋嫩,想象在曲院风荷的葱绿烟霭中,咀嚼银波碧浪的涟漪。从乡愁中寻回祖先、父母传下的魂魄和希望,还有下一代蓝色的梦想,在时光脚步中捕捉到蓝溪深处的生命喧响,从而坚定自己的求索。读者可以从她对乡愁的书写中觉察到当代人的情感诉求,并从中体味到惺惺相惜的精神共鸣。
湘西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张雪云没有忽略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进行了积极的艺术开掘,穿越时代隧道的屏障,领略到意味深长的哲学价值。蓝溪口面对的沅陵位居五溪山水交汇之所,荆南要冲雄峙之地,素有“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所谓“天下积储在楚,楚之咽喉在辰,辰安则楚安,楚安则天下安”。战国时,楚置黔中郡,屈原曾经来此,面对沅水感叹:“沅有芷兮澧有兰……观流水兮潺湲”;展救世安民之略的王阳明在此留下诗文;大唐而兴的龙兴讲寺的暮鼓晨钟依然在心中日日敲响,古城古寺,即使城墙不再,砖瓦难存,但凝望处蒹葭苍苍,让人获取某种庄严宁静、喜乐和力量。她常见的水边情形化作心灵的一个渡口,泊在月光下,那月光自然已有千年万年,自然会引人思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不知江月待何人”。灵性的山水,即是一本自古而来的大书,于沉默中散发出悠远的气息,给每一个端详的人以尊贵,以气度,以历久弥新的相思相知。
对人性的关照与体贴在《蓝渡》的字里行间比比皆是,体现了作者与普通人的密切联系,彼此相通的温情。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在张雪云的笔下,他们挑担背篓从沅水河边走入读者的视野:“早些年,我窗外的文昌码头处,是沅水流域一个重要的集散中心。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民将自己生产的桐油、菜油等农副产品从山里担来,驳船靠岸,到这里倒卖,……那些挑油的汉子,穿着对襟布衫,包着白布头帕,脚穿自制的草鞋,从弯弯山道上挥汗如雨而来。妇女梳着耙耙髻,背着大背篓,弯腰蹒跚而来,背篓里面装着板栗、花椒、木耳、黄豆、花生等各种山货。他们打着手势,嚼着土语,彼此交换着各自的生活所需与小小的欢乐。……他们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在水边忙活着简单的日子,……成为沅水流域独特的一景。”张雪云在多年从教的岁月里,关注的目光除了教室里的孩子们,就是市井百态:卖菜的婶子、摆地摊的小贩,大清早聚集守候雇主光临的中年汉子,常在烟雨潇然、人车混杂之间,泥泞湿沥、霉味弥漫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为生存奔波忙碌,或如蓬草,或如劲竹,却无论多么艰辛困苦,总能度过四季凉热,总有一份朴素的希冀与梦想。她以蓝溪为人生之河,揣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渡口,如自己的蓝渡。四季一如既往地变迁,流年似水无声无息,然而世间万物皆有自己渴求的境界,一条河有起伏变化的深浅,一朵花有自由开放的姿态,一棵树有别样的风骨,一个人的生命究竟应该赋予怎样的意义,要以怎样的跋涉,才能从自己的渡口抵达彼岸?
张雪云的文笔清婉朴实,恰如湘西山水幽深灵泛,时而若山静穆厚实,时而如水柔和细腻,且又酣畅淋漓。既能蹈大方,观大势,又能凝静气,清气氤氲。在书写中不乏对文体的探索,在虚实深浅或轻或重之间反复掂量,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张雪云与河流的对话、日前的问答汇成了这本散文集《蓝渡》。生活其实没有唯一的答案,所有一切都在不断的摆渡之中,她的文字和思考也因此偶见重复,但愿今后在重复之中更有新的拓展和发现,如此,或许她心中的河流将会更加澎湃,将会描画出更为深刻独到的风景。
是为序。
2019年4月于北京
(叶梅,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部分章节节选:
长在瓜秧上的本事
对于乡下的有些本事,我一直感到很奇怪。
比如,随便丢弃的一粒南瓜籽或是冬瓜籽,落在某个旯旮,只要有点乌黢麻黑的土,隔三岔五的雨水,隔不了多久,尖壳壳里就会钻出两瓣黄嫩嫩的芽来,软软的太阳一晒,嫩黄便成了浅绿,然后是,青绿、翠绿、深绿、墨绿。由浅入深的过程中,瓜秧牵了无数的须,玲珑曲卷,若是近处有枯枝或竹篱,必是葳葳蕤蕤的向上攀援,不再低三下四地匍匐。这种寂静生长的力量,既柔弱又强大,不需任何号令,也不需向谁招摇,自然而然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蓬勃了整个村庄与田野的生机。
后来,想到这尘世中的诸多人与事,莫不似着这瓜秧,有着与生俱来的本事。寂寂的生长,默默的消亡,一消一长之间,便有了繁芜缤纷的万千。
我出生的湘西大地,当属楚地。楚地多奇谲,楚人多幻想,可谓遍地巫风,神秘莫测得很。听母亲说,我小时面黄饥瘦,并不太好养,除了寄拜干爷外,还请过师傅“收黑”。师傅是蓝溪本村的,年纪有些大,孤孤寡寡的一个人,平日里目光呆滞,邋里邋遢,并不招人喜欢。“收黑”时,却全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双目炯炯,有异彩,口里咿咿唔唔,念念有词。师傅先是取了个量米的升子,盛上堆尖的一升米,米上插三支袅燃的细香,又用淘米水煮了鸡蛋。待鸡蛋熟了,点燃三根灯草,用桐油灯照着青花瓷碗里的水,光亮处,右手两根糙指轻捏了鸡蛋慢旋缓转,眯缝着眼死劲盯着,生怕闪了神。左手抻直了食指与中指,并拢如剑,上下左右轮挥几下,然后直指某个方向,“嗨”一声落座,鸡蛋竖立于升子米中。师傅闭目养神几分钟,然后说,好了,厌乌邪气都已去掉,孩子没事了。临出门时,师傅将法事中的鸡蛋,用红丝线裹了,交代挂在胸前,回后置于枕下,三天后方可万事大吉。说来也怪,过后不久,我便长了肌肉,也长了脸色。
一次,与母亲一起去蒙湖庙里看“杠仙”。仙娘是个妇人,三十几岁模样,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头乌黑的齐肩长发,穿一襟印花布夹袄,襟前绣有一朵好看的凤仙花。正是山野桃花、李花疯开的时候,人们脸上各自带了喜气呼朋引伴。请仙娘“杠仙”的人带了纸烛香草,极虔诚。约半个时辰,妇人突然浑身颤抖起来,面目陡变,南腔北调地开口说话。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杠仙了,杠仙了。”此时,仙娘以青丝绸巾覆了脸,半哼半唱的说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说到伤心处,说者涕泗横溢难以自抑,听者嘘泣不止,坚信不疑。更有亡灵生前语气腔调,前尘往事,在仙娘身上惟妙惟肖。这时的仙娘,似乎能自由穿行于阴阳两界,魂灵附体,实在让人惊骇。那晚,一弯新月漫在湖面上,湖水荡来漾去,嵯峨的山,影在湖中,忽高忽低,忽明忽暗。我与母亲,一夜未曾入眠,心里莫名的害怕,脸白得像一片恍惚的月光。
本村与邻村的一些匠人,木匠、锯匠、篾匠、箍桶匠、泥瓦匠,包括走村串户的挑担货郎、沿路乞讨的叫化子,多多少少都有些奇妙的本事。我老乡的舅舅是个泥瓦匠,为人厚实,掌得一手好窑火。有年冬天,正烧砖瓦,烧了三天三夜,窑火还是没有烧透。于是就问徒弟们,有没有人来过窑边。徒弟们想了半天,方才说,老前天是有个外地人从此经过,讨要一袋烟,我们没搭理他,他悻悻地走了。泥瓦匠心知肚明,二话没说,回家拿了把杀猪尖刀,点了一柱香,烧了半搭钱纸,口里边念叨,边用香纸凭空挥画,边用尖刀刺穿另半叠钱纸,最后“哦嗬”一声,尖刀串着钱纸飞掷到窑顶,稳稳插在窑田上。事毕,也不说话,只是抽着闷烟。第二天,一个辰溪人扑脚翻天的来到窑前,捧着胸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连道不是,其状,痛苦不堪,生不如死。
这些诡谲神秘的奇门遁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颇有些魔幻。我家乡这片神奇的土地,夹河高山,群峰竞秀,层层梯田,座座吊脚楼,美得心痛。河水清黝,滩多流急,沅江酉水号子,粗犷撩人,加之烟云包裹的幽谷叠峰,群鸦乱叫,莫不使人悄怆幽邃,凄神寒骨,神秘难测。想来,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流放沅湘时,肯定见识过。“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沅生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他把许多的见闻写进《九歌·山鬼》、《湘夫人》,开楚人多幻想之先河。不然,沈从文先生何以会说:“屈原虽死了千年,《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
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鬼的解释是:“魂之所归,谓之为鬼”。“鬼”发的是“归”音。于是,骇人听闻的“赶尸”在湘西应运而生。据说 “赶尸匠”赶尸时,先得在家里做一道符,符上有死人的生辰八字。赶时,先用“九龙水”喷洒尸体,然后将朱砂封住尸体嘴巴、鼻子、耳朵、头心门、前膛心、后膛心、左右手掌心,左右脚掌心这十个最容易灵魂出窍处,防止尸身魂飞魄散,再用符贴其额头,喊一声“起”,尸身便会急急如律令地站起来,一蹦一跳前行,且双腿不会弯曲。
“放蛊”则只有某些湘西女人才会,且多是中老年。湘西女人将蜘蛛、蜈蚣、蝎子等剧毒的虫子抓来,放置在大陶罐中,让其相互掠食,最后存活下来的则最具毒性,将其捣烂,再配上许多稀奇古怪的药引,比如易致人幻觉的鹤子草,含羞草根压出的毒汁,蔓陀罗花等。蛊毒进入人身体后,具有某种生命力,且受放盅人的控制。蛊毒一旦四处乱窜,不及时收蛊的话,则可致人性命。湘西女人的蛊,大多属捍卫婚姻,捍卫家庭,抑或捍卫爱情的“连心药”,沈从文先生曾深有感慨地说这“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这种 “凄、馨、美”的另类表现,也算是独步天下的湘西女人特有的本事。
至于辰州符,最是法力无边。沈从文先生在《沅陵的人》说到:“辰州符主要的工具是一碗水,一切病痛统统由这一碗水解决,一个死尸的行动,也得用水迎面而解。”辰州符的核心内容为符、诀语、字号,外加一碗水。四者同时使用,水是黏合剂,辰州符里的特技表演中许多惊险节目,如滚刺床、趟火槽、上刀梯、踩犁头等,巫师只需念“辰州符”,然后画符,喷水,则一切皆如常物。辰州符到底为何有些法力,又有些什么法力,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其实,这些玄幻莫测的迷团,有时,也未必有完全弄清楚的必要,待破解得清清楚楚,也就索然寡味了。所有的法力与愿心,无外乎是为了寻得某种力量,获取某种信仰,以期改良乏善可陈的旧生活。
天时常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山是有生命的,水是有生命的,土地是有生命的,村庄也是有生命的。一丛草是有本事的,一阵风是有本事的,一场雨是有本事的,一朵云是有本事的,一壶月光是有本事的,一蔸黄嫩嫩的南瓜秧子也是有本事的。坐在万物丛生的土地中央,我很好奇,也很喜欢这些生长的力量,等待的力量,回到故乡的力量,昭示力量的力量,哪怕杂糅那么多的神性和魔性。
这样想时,伫立在田野村庄,一汪清亮的蓝溪边的我,不再诚惶诚恐地害怕,内心充溢的是一些瑰丽,一些温暖,一些确切的向往。一些赤橙黄绿的本事,在家乡的瓜棚豆架下,缓缓的,依山傍水,滋长成一首清婉动人的歌谣。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