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湖南作家网 时间 : 2022-05-27
分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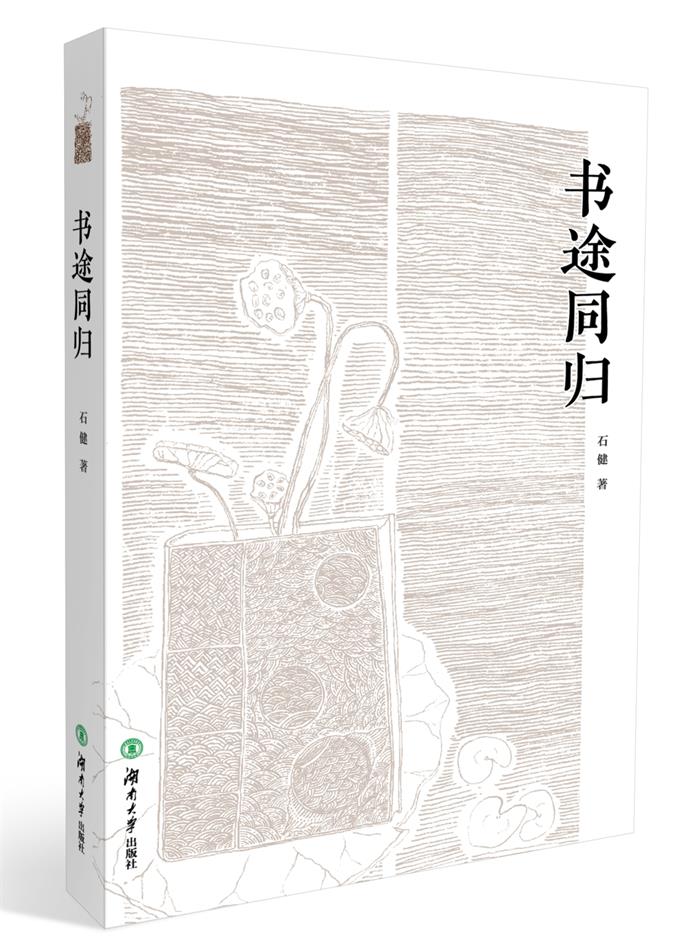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石健,湘西人,苗族,70后,主任编辑。任职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团结报社。兼任吉首大学客座教授,湘西州“书香湘西”全民阅读公益推广人;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七期中青年作家班学员。
从事地市报文学副刊编辑22年,以“文学保姆”为责任使命,以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赢得了湘西文学爱好者的好评。所编辑文学作品在省级和全国副刊竞赛中获得百余次奖励,其中,10次获得湖南传媒最高奖项——“湖南新闻奖”副刊奖。
工作之余,义务策划组织活动,公益推广全民阅读;读书之余,笔耕不辍,将所学所感所思凝结成文字篇章,散见于《中国民族报》《中国旅游报》《湖南日报》《团结报》《神州时代文艺》《中国记者》《闲人闲事》《西部散文原创》《湖南文学》等报刊,并有《关于书写的断想》《绽放成蒲公英的姿态》《连心路上故事多》等多篇作品在省级和全国副刊竞赛中获奖。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散文集。以读书生活为线索,串连起作者人生所经历的成长故事与命运坎坷。
本书并非文学评论集与读书扎记。所有与书籍、阅读相关的文字,讲述着斑斓多彩的书人书事,呈现着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情绪和心事,以及对丰盈心灵、艺术之美、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向往追求,还有对诡谲命运的不屈与抗争。
本书共分为五大部分:《序章》《岁华可读》《笔墨记忆》《纸页风华》《一字见心》《书途同归》,其中,既有自己的所读所历、所感所思,亦有身边读书人的故事与启示。关于自己,着重讲述了面对丈夫因病去世、自身罹患乳腺癌等重大打击时,书籍与阅读给予的强大精神慰藉和巨大力量支撑;关于他人,怀着深情讲述了湘西文化圈读书人们的精神追求、无私奉献、坎坷命运。
本书以读书为框架和明线,通过“自我”与“他者”的叙述、描写、思考,完成了对书途一路美好风景的再现,实现了抵御不幸、强大自我的历练,抵达了书路尽头的精神家园——灵魂的安顿之所、生命的避难之所。本书融感性的描述与理性的思考于一体,昂扬着精神之力与艺术之美。
著名诗人刘年为本书作序。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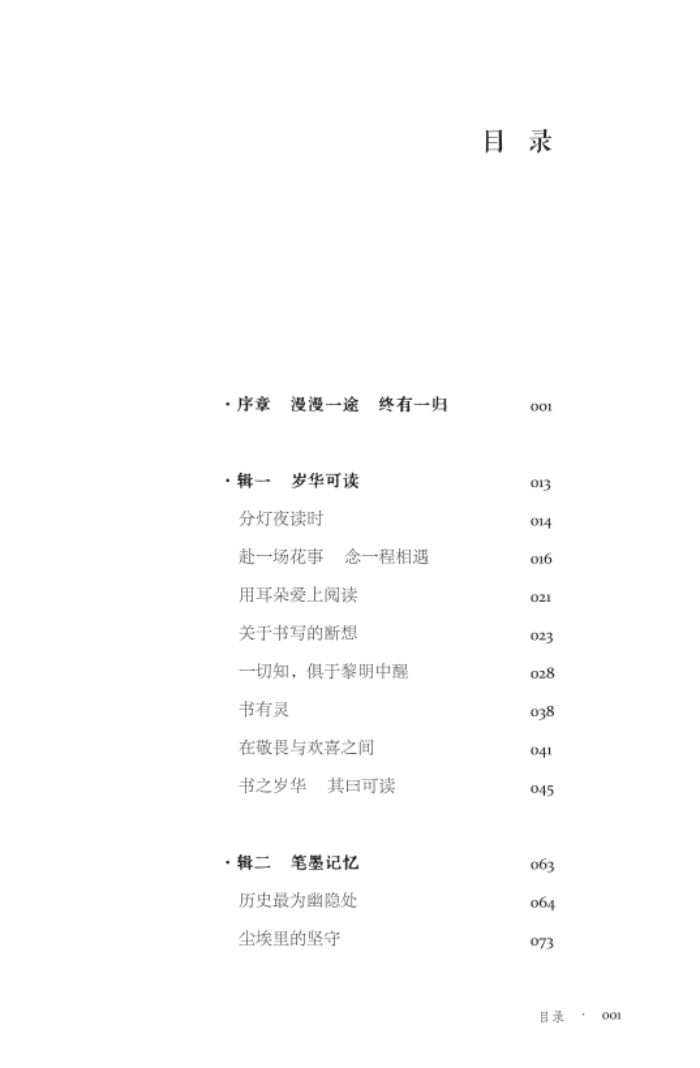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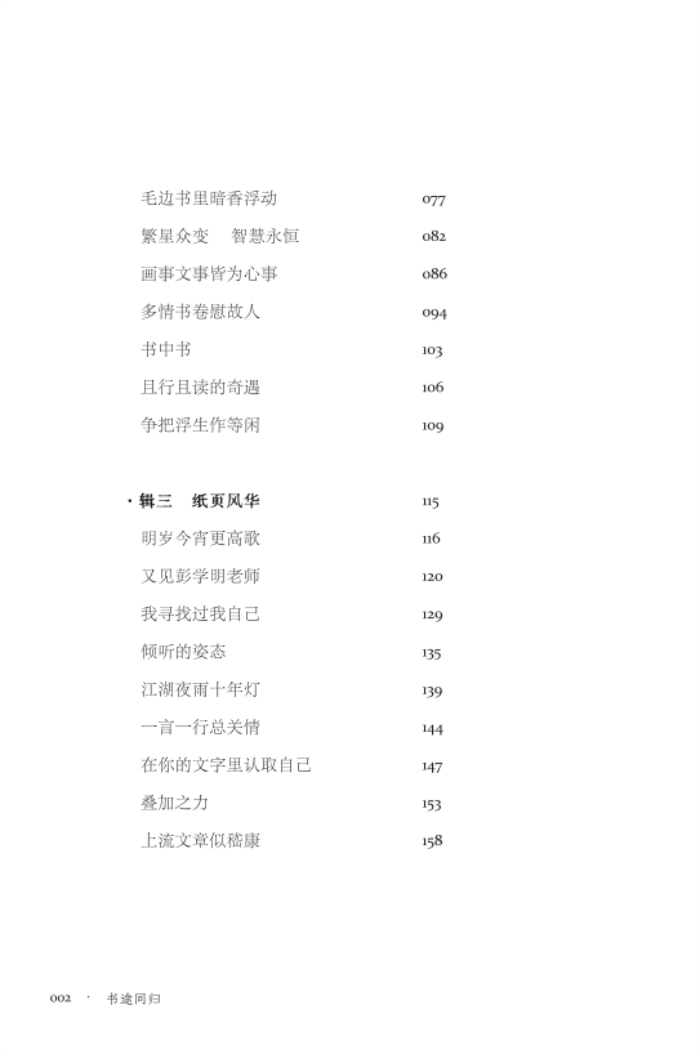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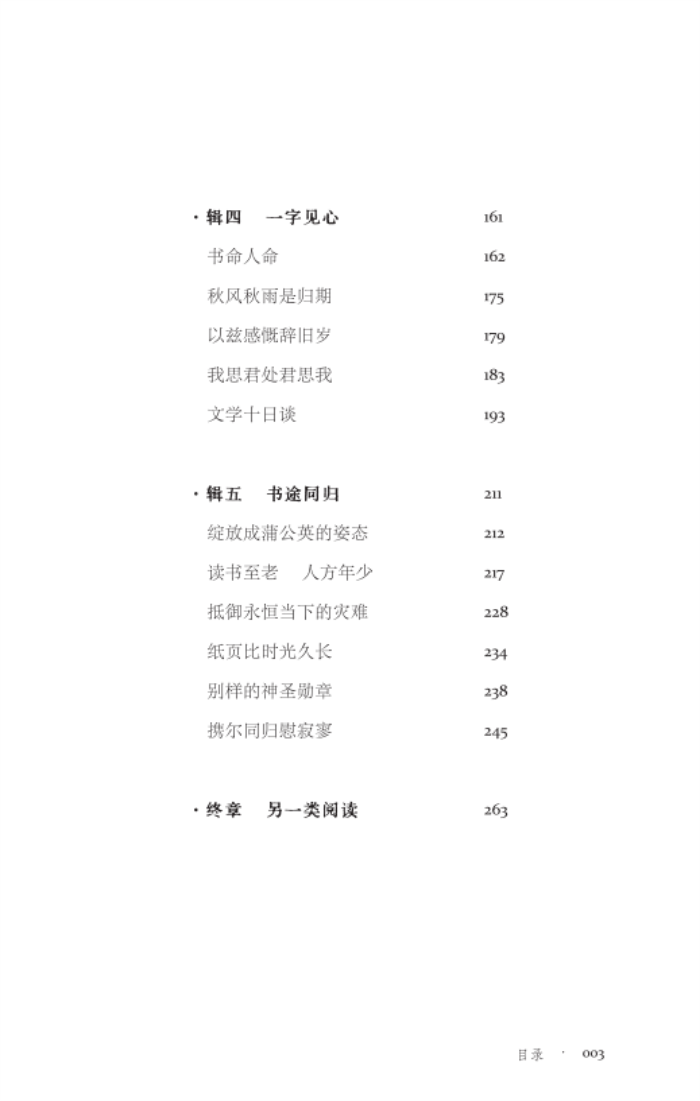
【评论摘录】
浅读石健
——代为《书途同归》序
刘年
1
浅读了打印本的《书途同归》,想象书中的女主角,应该是不事脂粉,带着淡淡的油墨香,热爱阅读和写作。与我熟悉的那座圆滑世故的看不透的吉首城不同,她是方正的,有棱角的,和汉字一样。
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孑然一身的女子,在这个荒凉苍茫的人世,挨了命运一记又一记的重拳后,竟然还顽固地相信着爱情。
2
“造化奇妙,书籍有灵”——石健如是说。
作家们的书是有灵魂的,或者说书就是他们的灵魂。同那些有趣的灵魂打交道,比在乏味的生活中与千篇一律的世人打麻将有意思得多。
因为都爱阅读,我们有了共同的朋友:苏东坡,博尔赫斯,荣格,尼采,嵇康,鲁迅,王小波,沈从文,李元胜,等等。因此,和她第一次见面,不必客套和试探,在车水马龙的吉首世纪大道上,我们直接谈及了彼此写作的终极意义——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而写,是因为有话要说,写作便成了生命的本能,是一生的价值和方向所在。
也许我们的文字都无法对抗时间,留名青史,但有它们作为证据,便可以向仅有的读者,向我们的亲友特别是子孙证明,我们曾经勇敢地活过,我们曾经不管不顾地爱过恨过,我们尽己所能倾其所有地追逐过梦想。
我们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只是作为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最后变成一个有辈分有生卒年月的名字,刻在坟前的石碑上。
3
“人是需要生一场病、历一场劫的。那些病痛、那些劫难让人得以审视累积在心灵上的尘垢,得以强悍身体与精神的意志,得以领受生命的本质真相,得以理解幸福的真正含义。”——石健如是说。
诗家不幸诗歌幸。石健患癌后写的那篇文章《携尔同归慰寂寥》,是向死而生的文字,传递的感情很复杂,有不动声色却已深入骨髓的孤独和疼痛,但更多的是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那是一种历经了人情冷暖、生死离别后的热爱,是通透的,是有根的,是坚定方向和强大力量的。
以至于,那个上午的见面,并没有去提她的病情,我不太会安慰,也想她不需要安慰,她看起来比很多健康的人还健康。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粉,看她井井有条地吃。也算是阅读吧,边阅读,边对照她的文字里所描述的动了乳腺癌手术后一个人在病床上看书看到痛哭的点点滴滴,暗暗地自问,至今还害怕医院害怕体检害怕打针的我,如果面对这样的病魔和手术,能不能挺过来……
有一瞬间,石健以为嘴角有辣椒末或者别的,取纸巾擦了擦。她不知道,我在读一首诗,赞美诗,赞美生命的。
4
为了印证自己的阅读感觉,那个将要离开吉首的早上,我特意叫她请了这碗吉首粉。
乾州古城里,只遇到一树樱花。十分之一的红,在树上;十分之九的红,在石板上。
如我所料,她的穿着、说话、做事,简洁、澹泊、质朴而真诚,与她的文字并无二致。不过她的头发,比想象中的更短,更白,提醒我她是个病人。
微风中,我们聊及喜爱的和讨厌的。她像一本书一样,轻易地打开了自己:
“我喜欢我的女儿心心妹,我喜欢和年轻的男孩女孩玩儿;我从小喜欢林黛玉,想到她就会哭;我喜欢独自出行,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我喜欢与大自然、小动物以及生活有关的细节……”
“我不喜欢无知无畏的人、随地吐痰的男人、打官腔的女人、吃饱了还在撑的人;讨厌写摊派的稿件,讨厌人多车多的地方,讨厌逼仄狭隘敏感的自己……”
人到中年,还保存着这么多喜欢与不喜欢的事物,这让我喜欢。
我警惕自己越来越多的包容和宽恕,觉得这是激情的丧失和圆滑的开始——我不想活成自己讨厌的人。
吉首粉是天下最好吃的米粉,她找的店,没挂招牌,显然有其自信的长处。果然,花样多、分量足、口味重。她特意给我加了一个蛋卷,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我平时的量。因为过于好吃,也因为不想浪费,我硬撑着吃完了。
吃完了,才意识到,不知不觉间又活成她不喜欢的人了。
5
后来才知道,其实以前在活动中见过她,而且不止一次。
只是自己没留意,或者忘记了。
她就是这样,在大街上,在人群里,在饭局中,你都很容易忽略。除非,你打开她的灵魂。
6
告别石健,骑车出城,下起了雨。
突然感觉这个春天,比以往都要脆弱,决定绕道矮寨,多看看花事。
有些山,以前觉得是乳房的,这次觉得都是肿瘤。
7
愿书,保佑文字。
愿文字保佑一个对文字如此虔诚的人。
以此为序。
2021年4月3日,辛丑樱花落尽时
此生原为读书来
——石健其人其书其文
九妹
(一)
《红楼梦》是读书人的青春王国。
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恰是贾宝玉、林黛玉初次见面时那般年纪。十三四岁读初中,学校很远,每次上学必是清晨乘船到县城,再辗转下午四点的班车去学校。近乎大半天的时间,我唯有躲在县城新华书店的角落里蹭书看。初中三年,竟然“免费”读完了一部近千页的《红楼梦》。
高中毕业时,语文老师赠给我一本锁线精装的《红楼梦》。这也是我的第一本藏书。工作后,辗转数个地方,扔掉了许多东西,但那本《红楼梦》一直被我带在身边,习惯每年春节时取出来随心翻阅数十页。
那年春节假期的某个午后,我坐在梅花树下读《红楼梦》,并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则消息。石健留言说:“我也有一本同样的《红楼梦》,父亲送给我的。记得是一九九二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淡赭色的封面上是宝玉与黛玉的线描像。”
记忆深处,读《红楼梦》的那个年月,我和石健如同大观园里那群天真烂漫的少女,是《红楼梦》将那些别人看来平淡的日子串成了我们生命历程中的珍珠项链,一点一滴、一粒一粒地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告慰我们或贫困或孤独的青春时代。
书籍的重要性,于石健和我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书籍,我确定与她将是永不能交汇的两条生命线。
二十多年前,我们都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任报社副刊编辑,我在乡村中学教书,山里山外未曾晤面。她一次次地编发了我投给她的手写文稿,还亲笔回信给我,字迹洒脱,空灵素淡,鼓励我借着文学的翅膀早日飞出大山。那真是世间最为美好真挚的期望与祝福。霍金曾说:“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是遥远的相似性。”如果没有遇见石健,肯定没有现在的九妹。我始终觉得,我与石健的相识,是命运的转折点,是人的生命的惊觉。突然的点醒,突然的转向,蓦然回首中,“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一朵花,一滴雨,都能扩散出一片暖融融的记忆涟漪。
石健的父母在高校工作,且因了母亲工作的缘故,从小她就常常一个人在图书馆读书。那栋由沈从文先生题写馆名的图书馆,是天地之间的一块净土,安放着她天性空灵的心神。这一点,我永远羡慕她。但她有时会幽幽感叹:“小时候过得太好了,把命里的好运气都用光了,所以后来才会遇到这么多事儿……”我原本以为,她是一个如同史湘云般洒脱率性的女子,没有想到她内心深处却是那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
“比如,少年时代看《红楼梦》,虽然那时还读不懂‘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关乎青春易逝和生命无常的深刻奥义,但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爱上黛玉,总觉得这个爱哭鬼正是自己的投影,甚至连哭的原因都同样莫名其妙、令他人生厌,但自觉也折射了多情、单纯、真挚、悲悯的心。”
——石健《书途同归》
读书是这样的:由自己体会出来的书中情事格外生动,毫无古今中外的时空隔阂。只是在《书途同归》一书中读到这段话时,我突然心疼这个已认识了二十多年的女子。她身为副刊编辑,几十年如一日,帮助我以及同我一样的文学爱好者,用文学改变困境、追逐梦想,甚至改变命运、超越自我,而她就像一盏香茗,将苦涩藏在心底,散发出来的永远是芳香。
有了微信后,偶尔也能在朋友圈见到石健年少时的照片。但见她着一袭素洁长裙坐在舞台上弹钢琴,钢琴的弧线古老优雅,而她在矜持地微笑。我仿佛能听见手指触碰琴键发出的旋律,优美动听,令人迷恋,其中有缱绻相依的情愫。还记得石健的另一张旧照片,她双手抱膝坐在校园的草地上,微微偏头做沉思状,眼神清澈,表情从容,留一头齐肩短发,远离俗韵,明媚如花,给人惊艳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打动我的那个美好瞬间,源自她读书人的静美、读书人的虔诚与安然。
对喜欢《红楼梦》的女子来说,县城的新华书店是“大观园”,高校的图书馆也是“大观园”,它们所承载的那些年、那些事,见证了我们成长的岁月,承载着时代的变迁,不约而同地成为我与石健生命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我们心里眷恋的一个青春王国。
发真归源,透彻中得清奇之致,石健注定会在“大观园”里绽放自己的生命之花。
(二)
终于见面的时候,我和石健皆过三十而立的年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某年,我把一方“书带草堂”匾额送给了石健,同时还送给她一本《曲院风荷》。匾额是女书法家方放题写的,草叶编结可护书而谓“书带草”,草亦尊经,墨影呈祥,“书带草堂”很是适合她这个读书人的。书为北京大学朱良志老师所写,购自北京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里的小书店。我专业并非学习汉语言文学,可以说是从阅读朱老师的书开始接触美学的。读他的书,我明白:原来美可娓娓道来,亦可欣赏把玩,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微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石健喜欢读什么,因为自己写古画大量地阅读艺术、美学等书籍,就把喜欢的书送给了她。
还好,石健是喜欢这本书的,且不惜笔墨记录读书之悟:“得承认,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美的书。从可视可触可感的文字之美、装帧之美、插图之美,再到形而上、非屏息凝神不得体察领悟的玄奥之美,从具象升华到抽象,从艺术理念落实到生活实践,无一不美。”
我喜欢石健的喜欢。正是朱良志老师的这一本美学论著,使人深深体会到美于生活无处不在,能否捕捉美、享受美,全在乎人心。真正的读书人常常是跨越边界地进行阅读,白纸黑字里结着无穷尽的因果网,影影绰绰,参差掩映,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亦是内心的一种震荡与回响。
我喜欢:“艺术家仅次于上帝。”
她认定:“艺术可以拯救一切。”
艺术之外,我们在现实中都过得并不轻松。儿子小学毕业,读初中、高中,直至高考,我在生活里是围着儿子转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即使淡泊名利,职场的尔虞我诈仍旧使人备觉心累。读书成为最重要的自我排解、自我修养、自我安抚。石健经历了人生中极其艰难的几年,女儿尚小,爱人离去,自身患病,亦需要寻一处幽静之所,静下心,读一本极静的书,将内心的静谧带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诚然,人到中年,书籍就像一处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委婉曲折中,蕴含着安顿生命的精神诉求与人文关怀。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我们交往多了起来,渐渐固定成为一个三五至友的书友圈。我们大多是在乾州古城的湘西文史书店见面,每次都会各买几本喜欢的书,逢年过节也给彼此送书,共同组织“世界读书日”活动,一起成为“书香湘西”全民阅读公益推广人,各自书房都悬挂着由省文化部门颁发的一块“书香之家”牌匾。
二〇二〇年底,我到北京故宫看画展,偶遇作家祝勇在故宫书店讲座并签售,我得以在现场签得一本书。后来想到石健特别喜欢祝勇,小迷妹一样称赞他“几近完美”,我便又回头再去签一本。当时书店已经没有祝勇的新书了,经理便从柜台下取出他正在读的一本卖给了我。再次走到祝勇老师面前时,我说:“我想帮我的朋友签一本书,祝老师能不能给她写一句话?因为我这个朋友病了……”祝老师抬头看着我,轻声地问:“签一句什么话好呢?”我愣了一下,忽泪涌,喃喃低语:“写一句祝福的话可以吗?”然后,他在扉页上面写下石健的名字,又题签了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那是他在现场签售唯一题写的一句祝福,山长水阔,任凭风吹雨打,希望读书人照样率性潇洒地过一生。那个时候,石健远在南方的哥哥家疗养。隔了很长一段时日,等她回到了吉首,我方才把书连同那一句祝福送给她。
因书关联,还有黄道贵先生主编的《闲人闲事》。
多年写作,我得以认识好些报刊编辑,他们同时也是作家,编辑之间互发作品是常见的事情。然而,石健是一个例外。我很惊讶她这个编辑,明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却除了同事和通讯员几乎未与外面的编辑交往。从事文学副刊编辑这么多年,她在湘西八县市有一大群作者。她关心他们,给他们编发文章,给他们讲写作课,义务指导初写者,给打工者寄赠文学书籍。二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湘西写作者都是从她主持的副刊成长起来的。她的交往是向下的、基层的,她的心灵是善良的、悲悯的。我感动石健推出了一大批湘西作家,也遗憾她这么多年来没有把自己推出去。
某一日,黄道贵先生向我约稿时,我把他推荐给石健认识。不想他们很投缘,石健连续给《闲人闲事》写了几篇书评——“看贵先生做书,我体悟到:琐屑庸常的生活可因闲心闲事过成诗,艰苦枯燥的工作亦可因闲情闲意变幻为艺术创作。”——闲闲道出,字字关情。我想,正是杭州的贵先生,以一种江南文人的方式,给石健打开了一道门缝,目光所及处,是品茗、酌酒、赏画、雅集。后来看到的她,夜晚来书店与我们喝茶,周末相邀去赏花,休假独自一人去大西北旅行,荡涤一切束缚,一任己心优游,近水远山皆有情,将生命的本真从遮蔽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从而洞见生命的明媚。
这个春花烂漫的三月,贵先生为《书途同归》设计出封面。线绘图案,背景是一席苇帘如书页对开,其下是一册书,书中斜逸而出几枝莲蓬,虽未着色,但艳艳绰绰,从幽冷的画面中跳出,给人惊艳的感觉。此图景,此情谊,使人感到深深的心灵契合,当为清奇之魂,也得清奇之韵。我想,石健的文字终如一朵花瓣紧裹的莲花绽放了。
(三)
石健是编辑,也是作家,更是文艺评论家。
二十二年前,报社新成立晚版部,二十四岁的石健自告奋勇投入了民生记者的行列;二〇二一年,报社设立新的版面《文旅周刊》,石健怀抱对新闻事业如火般的热情,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带病选择离开副刊,成为新版面的编辑,可谓再上新征程。虽非改行,但转岗也需勇气。当然,她的想法是要把《文旅周刊》也办出书卷气、文化味。让所有人意外的是,仅两年时间,她自己的一部著作——《书途同归》,华丽丽地闪亮面世。我作为第一读者拜读了此书,放眼全是清奇之文,文雅与风雅兼备,清净而不清高,远俗而不傲世,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萧散的、自由的、脱离物欲的气质,人间鄙吝的欲望、名利的渣滓,都不知何在,唯有一颗真实的心灵在婉转吟唱。
随着纸张在指尖一页页滑过,我情不自禁地幽幽慨叹。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石健应该不是不懂,恰恰是因为懂得,二十多年才一心一意地为人做嫁衣,实实在在耽误了自己的写作,耽误了一个才女趁早成为作家。
《书途同归》可以说是湘西第一本以“书”为主题的散文作品。不同于高校学术专题研究,也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散文结集,这是读书人的一本文化随笔,见才华,见性灵,见文化,见阅历,见天地、日月、星辰、烟云、人物、草树,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理想,也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
如果说做一个读书人是我的余生理想,那么石健则是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我粗略地记录,《书途同归》一书中,从《红楼梦》开始,石健写及的书籍多达一百二十六种,书名被我写满一张A4纸,密密麻麻,就像排列成一壁书墙。第一百本恰是《爱书人文选》,那是美国作家海莲喜欢的一本镶金边、上金漆的藏书,“能和我朝夕相处,至死方休。我甚至还能将它遗爱人间而含笑以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健的《书途同归》也是一本“爱书人文选”,她读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喜欢或者有着特殊意义的书,并为每一本书写下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文字,诉诸真情,宛若一次次心灵的歌吟。
从书目中可以了解到,石健和我都喜欢读张岱、沈从文、朱良志、祝勇等人的作品,但是,她读过的许多书是我不曾读过的,有的书名甚至不曾听闻。读《书途同归》,读她读的书,能发现她平时买书颇为挑剔,却会仍旧为别人送给她的书写下精彩评论;心存感恩,坚持读完亲朋好友包括她的学生们赠送的书;不忘旧人旧事,把学生留下的书一股脑儿搬回自己的书房;喜欢书店,再三写及湘西文史书店主人史金玉;等等。这一切让我想到西方一位作家的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传记性”是写作者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表现最充沛的心灵、最鲜活的感受。就此而言,石健实际上写出了一本属于她自己的人生之书。
与一般女性作家的文字不同,石健的文字比较理性,不拘于情情爱爱,遣文造句非绮丽、纤秾、含蓄,写书写人写事倒是可以套用“二十四诗品”中的“劲健”“悲慨”“流动”等词语,每一个文字都像饱蘸墨汁,晕染开来充满了意象,有一股天然的劲道和不假借人工修饰的美。如古时文人画家,石健并不是一个以工笔见胜的画匠,可她胸怀中自有天地,寥寥几笔,随手画来,便有一种扫清俗气的风度,技术上虽未必完美,可格调必是高的。又如中国古时才女,博通经史,能文善画,平时围着家人和灶台转,无机会为文,可是等到机会来临,随意写来,便是灵性至文,令人心折。
许是儿时学钢琴的缘故,石健一直热爱音乐,还由此写了好些关于音乐的评论文章,肖邦的哀而不伤,巴赫的谦卑沉静,莫扎特的精致灵秀,贝多芬的激情四射,使人感觉这个喜欢古典音乐的女子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让人不自觉地想要靠近。试着去听她喜欢的音乐,舒缓了我们的焦虑,安抚了躁动的心灵,与现代文化进行了精神上的对抗。我们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感受了“古典”的美好。她不仅文艺评论写得好,还特别健谈。每次读书活动,她的发言都最为精彩,不仅普通话字正腔圆,而且常常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总是惊讶到我。在我心中,她是湘西当下最有才气的一名女性文艺评论家。
平时在书店小聚时,也总能见到她给读者推荐书架上的书。在她的影响下,我甚至冲动地买了一套《博尔赫斯全集》,但除了诗歌,我几乎没有再翻过那些白色封面的小册子。然而,石健极喜欢博尔赫斯,我个人认为她在《书途同归》一书中写博尔赫斯写得尤其精彩。在《书之灵》里,她说“他是一位深刻的永恒的灵魂伴侣”,读书读到最后,正是此一效果与抱慰。在《携尔同归慰寂寥》里,她再次写到博尔赫斯。缘于病中读到学生李镇圻赠送的一本《老巴塔哥尼亚快车》,作者保罗在书中数次提到博尔赫斯,她亦将此当作是与七十九岁的博尔赫斯的一次邂逅,随着保罗的旅行拜会精神的偶像、寻求灵魂的皈依。“我觉得我们总是要试着去相信一些事,即使这些事后来让你很失望也无所谓”,博尔赫斯的话让她释怀,从而获得很多从容和安宁。
石健在书中写到的学生,还有小凌、勇智等,多是我熟悉亦喜欢的大学生,聪慧而懂事。另外,还有一位小朱,石健专为他写了一篇《书命人命》,字字沉重,深扣人心。我初次读此文时泪水潸然,再读时仍旧流涕叹惋。爱读书的小朱,患抑郁症的小朱,生命早逝的小朱,转眼即为空茫,瞬间翻为追忆,这人生短暂、生涯多艰的痛,让他的石老师哀婉恸哭,湿漉漉的文字裹着心扉的痛彻。真希望,泪水纷飞中,生命在白纸黑字中永生;轮回转世时,小朱变成一个风度翩翩的江南书生。
徐渭有一句话:“百年人做千年调。”在时光的河流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百年人,人无法摆脱生年不永的命运。但我知道,有生之年的岁月肯定是与石健在一起度过的,我们仍旧会年复一年地读书、喝茶、赏花。
书途同归,相信石健在读书写作的时候也得到了灵魂的皈依。
她本是——此生原为读书来。
写于二〇二二年四月一日夜
忽见石健转发一首李健的《四月物语》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