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湖南作家网 时间 : 2022-04-08
分享到:
【作者简介】
苏启平,男,1977年12月出生,湖南浏阳人。高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副主席,湖南省诗歌学会散文诗分会副会长。参加第十九届全国散文诗笔会,第三届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获第二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第十二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等。有作品在《星星》《散文诗》《诗潮》《山东文学》《湖南文学》《散文百家》等多种报刊发表。著有教育专著《教育是一场诗意的修行》等3部,散文诗集《回不去的故乡》等4部,长篇纪实小说《读谱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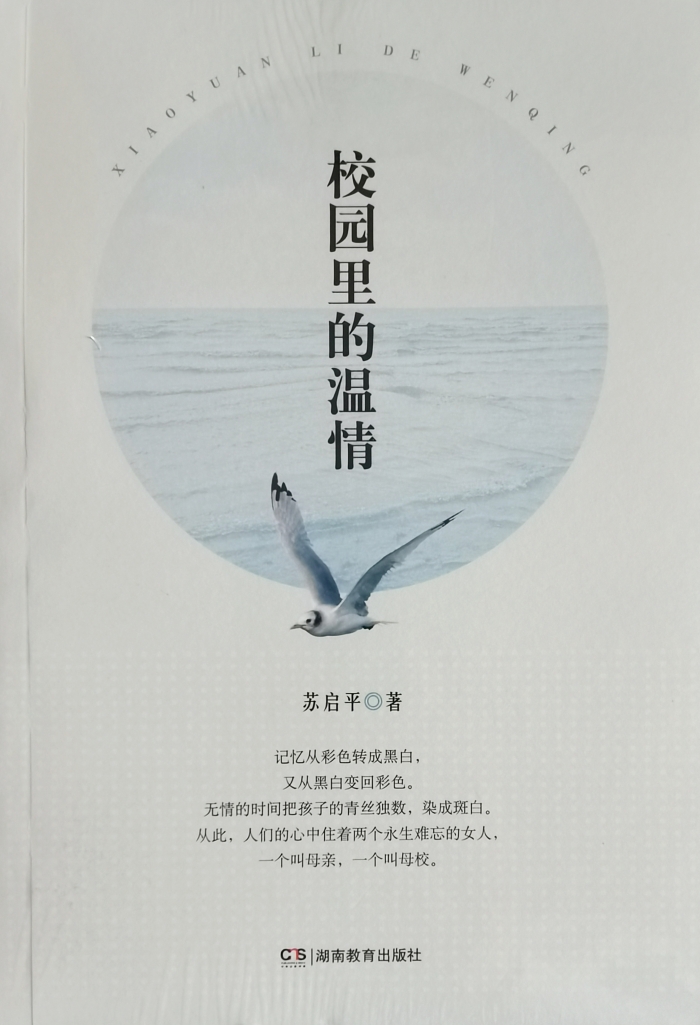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校园里的温情》2020年9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作者的第四部散文诗集,收录作者2016年3月到2020年6月之间所写的散文诗。祖国、故乡、校园,这是一位教师行走的出发与归宿。那里,藏着为人师者最美好的回忆与最深邃的思考。走过的路,是一种经历,一种学习,更是一种收获。
全书共五个部分,“河山锦绣”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秀美河山的热爱与赞美之情。故乡是每个人最难以忘怀的地标,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乡愁流韵”流淌着作者对故乡深厚的眷恋,以及无可奈何的痛楚。于教师而言,校园生活在美好之外还有着无限的期待与责任。“校园歌谣”有作者对自己校园生活的回忆,也有从教中对校园问题的困惑与思考。一位热爱诗歌的教师,自然也是一位真诚的抒情者,歌颂者。“真挚情愫”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赞美、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诸多感慨。作者同样也是一位思想者,探索者。“哲理之光”是作者在教书育人之余,以敏锐的视角,细腻的感触,发掘出的点点哲思,感悟独特,内涵丰富,可读性强。
【推荐理由】
作者是当代散文诗实力作家,本书的绝大部分作品均在各级报刊发表或获得奖励,一定程度代表着当代散文诗的较高水平。如《新城市人(二章)》等发表在《星星诗刊》,《敦煌笔记(四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书中另有组章发表于《散文诗》《诗潮》《湖南文学》《散文诗世界》《散文百家》等十余种报刊。《城市,与车有关的片段(组章)》获第12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挂国旗(组章)》在11.8万首诗歌中胜出获《诗刊》社“我向新和国献首诗”优秀奖。《汨罗江的脚步(两章)》获首届汨罗江文学奖。《山坡月》《张家界》等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奖。《悬崖说(组章)》与《山花记(组章)》分别是参加第19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与第3届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征稿中胜出的两组作品。书中的不少作品被选入不同的权威选本。《冬天记忆里的温情(组章)》 选入了王剑冰主编的漓江版年选。《山村物语》等被选入邹岳汉主编的现代版年选。序言与后记均已被《爱你·教师文学》、红网等刊发。
全书视野开阔,选材广泛。语言富有特色,准确凝练,生动形象,蕴藉深邃,意象丰富,抒情充沛磅礴,说理含蓄深远,叙述简洁明了,对当前语言文字运用有一定的示范性。作者能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研判是非,给人身临其境的在场感,并总有提纲挈领、醍醐灌顶的金句警句。作者是一个运用传统手法的高手,排比铺陈的画面,高度的拟人化,凸显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增添了文本的厚度,也增加了文本的耐读性。
【创作谈】
在故乡的影子里吟唱
苏启平
诗歌应具有语言美、音乐美、意境美,同时应闪现灵动的思辨,跳跃的思维,优美的文采,真挚的情愫与深邃的哲理。我的文字不一定能呈现诗歌的全部特点,但一定是真实的,不做作,不虚假。写作源于生活,真情是一切文学体裁的共性,诗歌自然不能例外。在我简陋、质朴的文字里,你可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生活留下的痕迹,听见我内心真实的呼喊。
故乡是我永远无法走出的梦境。12岁的时候,我用稚嫩的小手抄录了我的第一本诗集。我那双从未走出故乡的小脚,已经熟悉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在诗集里,我开始用尚未变声的童音吟唱我喜欢的故乡的一切。这如同我的初恋,朦胧而羞涩,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之后的几十年,我读高中,大学,参加工作,一步一步地远离故乡,故乡却始终挺着厚重的腰板站立在我记忆的中央。
我读自己的诗歌,如同一次又一次地返乡。梦里梦见最多的是我故乡,诗歌里写的最多的也是我的故乡。我也弄不清楚一个大男人,一个未真正远行的人,为什么会对故乡有如此深厚以至于无法抑制的情感。一般来说,只有那些从地域上远离胞衣地的人才会对故乡有深刻的领悟与独特的思索,有浓郁的离愁与磅礴的块垒。比如从小桥流水的江南去了飞雪连天的大漠,从蓝天碧水的海疆去了牛羊遍野的草原,自然风光的鲜明对比,风俗人情的极大差异,理所当然地给人不同震撼与情感。而我只是沿着浏阳河走到了湘江,一路的行走,均还在故乡宽大的怀抱之中。
要抒发真情,首先要自己是一个真实而情感充沛的人。弄懂了这个道理,我就不会诧异自己为什么一边观看感人的影视,一边泪流满面。为什么可以为了17年前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甘心情愿为他做贷款担保,却替他背下了沉重的债务。我曾经对一个我喜欢的女孩说,我对她的感情像我对故乡那么深。不理解我的她最终生气地离开了我。这恐怕要成为我一生中被他人最大的误解。我不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但我是一位真实的抒情者,对故乡尤其如此。感恩故乡的情愫一直如浏阳河之水,弯回九转,在我心中静静流淌,从未有片刻消逝。我对故乡的一草一木充满感激!杨柳、燕子、水稻、月亮、炊烟鲜活地生活在我的记忆里,伴着故乡那条永不干涸的小溪一路吟唱,一路欢歌。记忆深处还有我儿时的伙伴与乡亲,那渐渐模糊的面容就像青瓦之下褪色的屋檐。风沙苍老了岁月,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情谊。童年的往事如同一股亲切有力的血流在身体里永不停息地流动。
如果只是感恩,我依次写完《阁楼上的樵歌》《回不去的故乡》两本书也许就停笔了。可是我对故乡的感情与冲动至今丝毫不减,越是高兴的时候我就越悲伤,越是兴奋的时候我就越沉默。我的散文诗里多了一份似乎与生俱来的忧郁。不知何时,我对故乡多了一份愧疚。从2009年发表的那组《失落的山村》开始,我内心陷入了对故乡过去与未来的两难选择。过去的故乡是陈旧的,熟悉的,这是我永远无法复制的记忆。未来的故乡是时尚的,先进的,也是我们便捷生活的必然,这是我无法回避与拒绝的时代。我知道故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成了我内心的痛。我只能用颤巍巍的手把过去的“井水”,甚至一块“菜地”捧出来,又用战战兢兢的心与现在去衡量比较,发表一点我的感慨。故乡,对我恩重如山,对于她的改变我却无可奈何。就像我们的父母终其一生为我们守护,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苍老,走向死亡,我们作为子女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苦我想只有亲历过父亲或者母亲去世的人才能体会。是的,故乡就是我的至亲,我的父母。我要倾其一生为她吟唱,为她高歌。
祖国也是我的至亲。喜欢读中国史,就像用崇敬与感恩的心翻阅家谱。喜欢旅游,在祖国大地游山玩水,就像亲戚之间愉快的你来我往。我发自内心地深爱祖国与人民。2017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有幸获得了中国网推选的一个“中国好校长”奖项,会前主办方组织了一个校长思享会,我发言时第一句说的就是“我爱我的祖国”。无论是做班主任还是做校长,我都会毫不掩饰地告诉我的学生,我是那么热爱我的国家。这样就不难理解我的散文诗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秀美风光、英雄人物的组章。
每次去一个地方,我都要为那里最动人的风景写点文字,这成了我的习惯与纠结。说它是习惯,那是一种自觉。从2002第一次去桂林回来,我就写下了《桂林两章》。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直至今天。2019年8月,我陪同母亲、岳父、妻子、两个女儿去青海甘肃旅游,十天的时间,我自驾3700多公里,晚上依然坚持记录白天的点滴,写下了26首诗歌。说它是纠结,因为这似乎成了一种自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本应是一种轻松的状态。因为自己的纠结,去过后如果不写点什么就成了身上背负的沉重愧疚。我要感谢这种愧疚,是它让我用我笨拙的文字记录下了我深深的履痕,美美的历程以及对祖国盈盈的爱意。
走过的地方多了,我便有意识地去收集同类的素材,写同类的风景。“四大名亭”“十大名楼”“十大河流”“五岳名山”,我用我浅薄的知识,狭隘的眼界去审视这些名家多次吟咏的风光,竟然也有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感受。我喜欢这种若有所获的感觉。这激发了我写作此类素材的热情。我开始用这个经验写故乡,写故乡的山山水水。我尝试用散文诗这种特定的体裁,对浏阳河畔及主要支流附近的景点特产、名胜古迹进行另类视角描写,于是有了后来成书的《浏阳河畔的乡愁》。
校园注定了是我一辈子的念想。儿时兄弟姐妹游戏,我最喜欢的是扮演老师,教这些弟弟妹妹。后来如愿以偿,果真成了老师,还做了校长,在学校一待就近二十年。我只是长着让人欢喜的脸蛋,内心并不如旁人眼中所看到的那般外向与自信。我害怕在陌生的环境里待得太久,不习惯与陌生人说话,也害怕把自己最煽情的言语表达给该表达的人。我喜欢用自己默默的行动,与无色无味的时光去呈现我浓郁的情感与痴爱。正因为如此,我害怕去写我最熟悉的校园,就像我一直想写自己过世的父亲,却不敢动笔。莫非我就是那只火中取栗的猫,伸出爪子一次又一次试探着去抓火中的栗子,却最终一次又一次疼了自己。但是,我就是我,思前想后的挣扎过后,压制住急躁与不安,还是迫不及待地表达着我对校园的眷念与怀想。《晨读里的蟋蟀声》是我在《星星·散文诗》发表的第一章诗歌,这给了我鼓舞与信心。校园的生活是难忘的,尤其是读书的那些日子。在我们求学的年代,我们小山村的物质还不是很发达。学校的记忆除了学习的快乐,更多是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上学路上满地的泥泞,篮球场上漫天飞舞的灰尘,冬天糊满了纸的窗户,雪地冻得发痛的脚尖……校园给了我知识,未来;也藏着我的痛苦,秘密。
我们穷其一生的写作,只不过是与几个精妙词语,几枚哲理火花的邂逅。大千世界,蕴藏万物。我经常和夜同步,夜越深,我越安静。夜晚十一点之后的时间好像才开始属于我自己。我像一个性格孤僻的孩子,躲开嬉闹的伙伴,独自一人来到自己的小屋,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精心收集的玩具,一个一个地轻轻抚摸,尽情玩乐。城市、农村,一句话、一个人,一个镜头、一点声音,一朵花、一根野草,都能给我独特的感受。我看似坚强与笃定的外表下面,是柔弱而悲悯的内心,我用我并不细腻的情感去感悟我遇见的世界。世界给了我精彩的生活与蓬勃的诗意。
夏夜,我习惯坐在故乡晒谷坪的中央,看月亮慢慢升起,于是有了《山坡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未来教育家高研班的时候,多次坐高铁在北京长沙之间往返。高铁穿过丘陵山地的隧道,在宽广的北方平原呼啸而过。远方的路,山里的坟,给了我与众不同的思考,于是有了《大地的脸》。我习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我所看到的尘世,然后把收集到的信息,像粮食一样储藏在我不为人知的内心仓库。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是我思维的酵母。最终我把这些琐屑的所见所闻酿成了一壶酒,一壶自以为是的好酒。这使我想起来一千多年前我的祖先苏轼。尽管在哪个时候粮食是珍贵的,私自酿酒是不允许的,但他还是喜欢酿酒。他最终用他跛脚的酿酒技术酿出了并不好喝的酒。我能理解苏轼当时的仰首高歌,手舞足蹈。酒虽不好,但毕竟酿出了酒,有酒可喝。
我对世界与生活的感悟,恰如先祖酿酒的心态。其实不仅仅是这些感悟,这些散文诗,我对自己所有的诗歌与文字,都是这样一种心态。清代况周颐在他的《减字浣溪沙 听歌有感》里写到“他生莫做有情痴,天地无处着相思”,于故乡、于祖国、于校园,此生我定然是个情痴。
本文为《校园里的温情》创作谈(苏启平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2020.9出版)
【评论摘录】
乞灵于故土的丰饶之赋
——读苏启平的散文诗
江星若
散文诗作为独立而成熟的文体,始于波德莱尔于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巴黎的忧郁》。此后西方传统中的散文诗一直是一种反叛性的文学体裁,它反抗古典主义的文体规范,强调个体意识的在场和抒发。时至今日,当我们读勒内·夏尔、蓬热、博纳富瓦、雅贝斯等人的散文诗,会感到西方的散文诗依然是最具先锋性、试验性和个体隐秘性的文体之一,很难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散文诗是通过新文化运动进入中国的,作为一种宣释生命内在体验的文体,散文诗很符合那个时代个性解放的精神需要。然而随着启蒙时代的结束,很大一部分散文诗作者的写作逐渐偏离了上述激进传统,转而向中国古典文学中“赋”的传统靠拢。赋(尤其是西汉大赋)是一种可以与日常语言保持距离的文体,其语言中抒情性和描述性的成分远大于陈述性,在文字上也显得古奥典雅,这种特性使得它为描述的对象赋予了格外庄重铺陈的语调,因此汉赋具有纪念、称颂、煽动等诸多为事、物加成的社会功用。和赋的语言策略类似,当下很多散文诗作者也是通过一种诗化语言,和日常用语保持格调上的距离,以此来对日常生活进行诗审美。散文诗也成了迄今为止,中国传统的赋、比、兴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种体裁。
苏启平的散文诗可以说得上运用传统手法的一个范例。他的作品中常有这种排比铺陈的画面:
溪水蓄势,向天空飞去,摔落在深邃的峡谷。
草木虚怀若谷,张开手臂抱紧河流。落叶频频飞过山涧,犹如落红。
阳光洒落大地,田野沸腾。初夏带走村庄遗落的荒芜,秧苗青青。
鸟肩并肩组成最为壮观的交响团,奏响春天的乐章。初月,黄牛对着流星许愿,蛙声一片。
——《静听溪水》
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将乡间原野分解为一个个鲜活的画面,又将这些画面进行一种近乎自然的组合,这是典型的属于“赋”的铺陈手法。其抒情功能虽然略显单一,但与单纯的乡村风光却十分相宜。
“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被赋予过很多含义,但从字源上说,“兴”通常被认为与古代的宗教仪式有关。《说文解字》谓:“兴,起也。”商承祚认为兴的甲骨文“象四手各执盘之一角而兴起之”,此中的盘即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又陈世骧以为盘尚有“旋游”“舞踊”之意,因而“兴”可能意指“初民合群举物旋游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共同举起一件物体而旋转”。由此可见,“兴”作为一种文学手法,在起源上即具有两大特性:其一是带有宗教祭祀色彩的神秘主义,其二是以美好兴奋为基调的情感抒扬。“兴”被孔子列为诗歌的第一功用,尤能体现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史诗传统的抒情特征。因此“兴”一直被当成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一个根本范畴,相关的研究、著述不绝如缕。对许多中国的散文诗作者来说,“兴”这个审美基因正是牵引他们偏离西方先锋传统,回归到中国古典式抒情最主要的文化向心力。
苏启平的散文诗鲜明地体现出了上述“兴”的特征。例如他笔下的月亮就是一个起兴的重要意象:“月亮是我的理想。没有月影,哪颗星星可以搭载着我沉重的思绪周游宇宙?”(《钻进城市的心脏》)而“我”正是一个“半夜被月光唤醒的书生”。(《窗》)月亮就像一个神秘的主持人,拉开期待已久的幻想的序幕。在《山坡月》中,他这样描述月亮升起后的景象:
高矮不一的山峰相拥静坐。无数有名字和没有名字的虫鱼鸟兽,盛装出席。溪流用独特的嗓子放歌,藐视山间所有的乐手。
水稻蓬勃,压抑不住田野之上的蛙声。萤火虫围着树影乱舞,头顶星云密布。
一条壁虎在茂盛的枝叶间露出狡黠的笑,山兔晃着脑袋遥望东山之上。
读者不难发现,以上文字中的山峰、溪流、虫兽等都不具备写实的性质,而是被高度拟人化。比如,用“笑”这种壁虎不具备的属性去刻画一只真实的壁虎,而摇头晃脑的兔子也只有在动画片里才会出现。作者将动物变成人,并描绘了一幅具有魔幻色彩的月下狂欢图。这样,一方面呈现出美好欢乐的画面,另一方面又透露出作者内心孤独的底色——因为孤独,动物才会被刻画成人一样的伙伴的替代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切不可被文字的表面所迷惑。文学作品的深刻程度,往往取决于它文字背面的东西所能抵达的地方。
我印象中的浏阳是一个被山丘、河流层层屏护着的地方,从长沙去往浏阳要经过好些长长的隧道,似乎上天有意把这片青山绿水和相距仅70公里的省会城市隔绝开来。浏阳的农产品特别丰富,每次去都觉得舌头掉进了天然的味觉蜜罐,怎么都舍不得拿回来,浏阳的酒和烟花更是闻名全国。因此我很能理解为何在苏启平的散文诗中,乡村总是被形容为一个美好的精神乌托邦。作者的教师职业也使得他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故乡和童年就成为了他笔下最频繁的主题,也是他希望通过诗意去“唤醒”的一种生命体验。我们知道汉赋是源自于楚辞的,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正是屈原对反思现实而生发的各种浪漫想象。作为一名湖南的教师作家,苏启平在他的散文诗中延续了这一传统。在他笔下,幻想对现实的抗争,被表达成逃离物欲横流的城市、回归淳朴丰饶的故乡这样一种深沉的向往。
从我手头仅有的文本来看,“城市”一词在他的散文诗中出现得不多,且多半是作为乡村的陪衬,但细读之下就会觉得,他对乡村的抒写其实是以城市为基点的。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聚集着梦想和欲望的矛盾体:
繁华的城市,向我们扑面而来,措手不及。
树立的理想,如同高高的电线杆突兀挺拔。
——《大地的脸》
“陨石是星在地球的眼泪 ,梦想的内核一定坚硬无比”(《梦想》),梦想是他所力主歌颂的,尤其作为教师,为学生圆梦本就是他的职业;但成功永远只属于少数人,梦想的失落尤其令一个圆梦者难以忍受:“庸俗的社会变本加厉地按照金钱、名誉、利益吹皱水波”(《可爱的浪花》)。求而不得的梦想,最后就变成了奴役人、折磨人的欲望。在通往城市的列车上,他发现:
车厢里无数的面孔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们神情呆滞,从不言语。
——同上
这个细节非常形象地写出了现代人的异化和孤独:城市把人变成了面孔雷同的“乘客”,抽象为一堆身份、职务和编码。接下来,他用火车穿过隧道时忽明忽暗的体验来象征城市生活中价值混乱的状态:“记忆随着列车穿过隧道,用自己的身体感受白天与黑夜,混淆黑白。”(《大地的脸》)正是城市生活中遭遇的迷茫、孤独和疲惫,迫使他频频回首,在淳朴自然的乡村里寻求藉慰和解脱:
我一头钻进城市的心脏,只看到了几粒干瘪的秕谷,稀疏的散落在沟壑密布的心扉。
谁做了城市的硕鼠,偷走了我的稻子与蛙鸣。
密密麻麻的房屋能遮掩我的身躯,却怎么也装不住我泥土的气息。
走了,又回来,我始终走不出乡村低矮的篱笆。
——《钻进城市的心脏》
现实的城市和梦想的乡村这种二元对立,构成了他写作的基本张力。他张开双手,“一边插进了物欲横流的街市,一边触摸着清静甜美的灵魂”。(同上)城市生活越是机械化、职业化,人就越是向往一个充满神灵和感应的乡村:
心与鸟一起飞落在田地旁边的树丫,一声惊响,鸟飞走了,心还在。人类不是无所不能。
夜幕中,将手高高的举起,抓一把乡愁的种子,用力撒落在地里。
——《菜地》
现代文明虽然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相反,它让人类丧失了鸟一样自由飞翔的精神想象力。而要挽回人的自然天性,就需要“抓一把乡愁的种子”,让精神在乡村的泥土里扎根。因此,他乞灵于乡村的自然和春天,以唤醒在城市生活中日趋麻木的心灵:
杨柳与水择邻相处,风拐个弯,便以春天的名义为媒。
水在风里波澜微皱,杨柳在心里泛起涟漪。
所有灵动的事物分外敏感。敏感是密密麻麻的虫蚁,爬上了掌心。
——《风吹杨柳》
前文提到的“兴”,具有祈祷或者祭祀的神秘主义特质。正是这种对于失落神性的向往和祈求,使得苏启平的散文诗与“兴”的传统产生了共振。因此,他笔下的乡村和童年都不是写实性的,而是被赋予了精神乌托邦的意义,总是一派欢快、丰饶、淳朴的伊甸园景象。在他眼中,“村庄的天空比最繁华的都市更加热闹”(《四季不分的梨花》),“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无处不藏着与生俱来的亲切”(《心有田园》)。这也使得他的散文诗感染了“兴”所具有的那种美好、兴奋的情感抒扬。在《捕鱼的男人》中,作者塑造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梦幻人生,显然是他心中理想自我的投射。他甚至进一步地设想,土地中也许潜藏着比单纯的田园牧歌更加伟大的神意:
是否每一块土地都有一个自己的王朝,犹如人类汉唐的强盛。
我想写一部伟大的史书,记载这块土地的斑驳与灿烂。
——(《菜地》)
与此同时,他又不无矛盾地意识到,自己所构建的乡村伊甸园并不是真实的。他会追问自己:“五颜六色的瓜果,是否真能搭就我心中多姿多彩的田园?”(《心有田园》)他明白,童年记忆中美好的故乡只是无可挽回的梦:“故乡的水井是老人失落的眼。没有了昔日的光亮,却依旧流着眼泪。”(《水井》)
《西瓜地》写小时候到西瓜地里偷瓜,同样蕴含了一种现实和幻想交织的视角,偷瓜虽然“让你我有了一辈子回忆不尽的甜美时光”,但这一行为本身,从现实和成人的视角看,却是一种“错”。恰恰是“美丽的错误”这样一种悖论视角,让偷瓜这个行为具有了更丰富和耐人寻味的含义,也让《西瓜地》比那些单纯赞扬乡村美好的篇章显得更耐读。
苏启平还写了一些人文风景题材的散文诗,其中不乏闪光的句子和思想。例如:“楼基如同一枚印章,重重地盖在中华文化的中心”(《钟鼓楼》),对西安钟鼓楼的比喻非常传神,也厚重。总体来说,这部分作品多半是对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的铺陈和颂扬,走的是传统文人慷慨激昂的怀古路线,但主观情感和人文典故的结合略显生硬。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用了很多“血脉”“肌肤”“经络”这样用来强行刺激身体感官的词,以此拉近文化意象和主体的距离。从部分描写风景的篇章中,也能看出他有把“乡村乌托邦”的写作理念扩大到历史人文题材中来的想法。
苏启平的散文诗写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在构建乡土乌托邦对抗都市生活的同时,也对现代性的写作观念产生了一定的排异反应。这种写作立场为他的作品带来了唯美的特性,但或多或少造成了风格和手法上的单一。这也是当下中国散文诗和散文诗人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要摆脱这一困境,有赖于像苏启平这样优秀的散文诗作家,进行不断的思考和探索。
诗人郑敏曾说:“……高层或多层的诗的结构是现代派诗,尤其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这种结构是与诗的特点不可分开的,是使得诗不同于散文、小品文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在现代诗中,意象和意象之间不是罗列式的排比,而是彼此在意义上存在质的差别。诗歌文本就是要在上述差别所拉开的缝隙中不断进行跳跃性的审美。而在我们时下的大部分散文诗中,溪水、草木、大地、飞鸟、月亮等诸多事物总是保持着平行关系,各意象之间很难生发出相互渗透,层层递进的含义,也没有通往更深的本体论层面的隐喻。是故,中国散文诗在继承赋、兴等传统手法的同时,如何汲取更多的现代性元素,在古典式抒情和先锋性文体之间建立平衡,是摆在中国散文诗面前的重要课题。
其实,文学的现代性不等于社会的现代化。相反,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文学家在对人性异化的抵抗中建立起来的,它不是乡土文学的敌人,而是同盟。
(江星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作家)
湖南省作家协会 | 版权所有 : 湘ICP备05001310号
Copyright ? 2005 - 2012 Frguo. All Rights Reserved